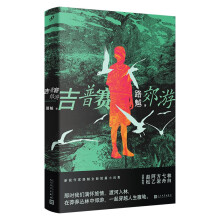《紫楼》:
“下次,下次会演我是不会来啦。”
上次地区会演后,县文艺宣传队就要解散时,鲁阿芳不止一次这么说过。可是这一回县文化馆重组文艺宣传队的通知刚发下去,她就进城来了。
“沙老师,我又来了。”鲁阿芳上了紫楼,一见到文化馆里负责文艺的沙中金,便红着脸笑着说。
“好了,台柱子来了。我还正愁着你不会再来了呢。”在窗前办公桌旁坐着的沙中金丢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迎着鲁阿芳。
她觉得他还是那么瘦。
瘦削的沙中金依旧穿一件厚厚的青布棉袄,罩着发旧的藏青外衣,罩衣的扣子不常扣。脸由于瘦显得有点平板,颧骨高高的,初见生人时,颧骨那一块皮肤微微泛点红色。
这时的沙中金脸上也泛出了一片红。
“我能算什么台柱子?沙老师真会说。前些日子听文化站刘站长说到要会演,还想着今年文艺宣传队不知要招哪些新角儿了,总不会还是几个老面孔。哎,沙老师,这次都选了谁呢?”
沙中金就一个一个地报了名字,基本上还是往年的老班子。鲁阿芳听了,叹了口气说:“真想过不再来了,演了多少年的剧,人都演老啦。接到通知的那一刻,队办厂里就有人说:‘阿芳,你又要到城里去啦!’倒像是我要变成城里人了。其实还不就是集中一时演剧吗?想到将来还是要散的,像上次那样哭哭啼啼地分手,心里总不是味儿。不过,我还是来啦。人活着,过一天是一天,就想着再到这紫楼上来聚聚。”
鲁阿芳是笑嘻嘻地说的,沙中金也是笑嘻嘻地听着,那话中分明带着一点悲哀的意味,只是说者和听者并没有去体会。也许这番话的意思在他们心中早已翻腾过不知多少回了。
文化馆的楼原是一座古旧的庙屋,很有些年头了。木梁,木檩,木楼板,木窗,连山墙也是木板钉的。板上刷了漆,那漆上得有些年头了。漆皮剥落了一些,远远望去,红色显旧变深了,像是紫色。文艺宣传队的那些女孩子,就叫它紫楼。
鲁阿芳家在盾山。江南丘陵山区,并无深山老林。盾山也算作大山了。其实坡度很小,绵延而上,山区里生活的人都行如平地。山里大多是红质土,生长着竹、松、杉。
沙中金不常到山里来,他总是在蓝云湖畔的几个公社选演员。那里人的口音就是纯地方戏的语味,他们有唱戏曲的传统。据说蓝云湖的水养嗓子,所以出了好几个名角儿去了省剧团。碰巧有一次,鲁阿芳的公社文化站搞会演,刘站长硬拉了沙中金来。沙中金一声不响地看了鲁阿芳演的节目,颧骨那一块皮肤不断地红上来……直到鲁阿芳演完下了台,他突然一巴掌拍到坐在旁边的刘站长肩上。
“你从哪里偷来的宝?”
刘站长耸了耸被拍的肩头,笑了:“自家园里长的哟。”
“你这里不该有,不该你这里有的……找她来,我要仔细看看。”
鲁阿芳奔奔跑跑地来到沙中金面前。那时她梳着两条小辫子,脸上还残留点没洗净的胭红,叫了一声“沙老师”后,脸上就越发地红起来。
弄得老练的沙中金好一会儿才想出第一句问话。
原来鲁阿芳的母亲是从蓝云湖畔嫁到盾山山区的。
当时沙中金就告诉鲁阿芳,县文化馆就要组织文艺宣传队了,到时会通知她去参加。
“我没进过几次城,还不知文化馆在哪里呢。”鲁阿芳带笑地叹着气说。
“好找,下汽车后一条直马路,就在马路边一座紫色的楼里。”刘站长认真地告诉她,好像她已收到了通知。
以后一段日子,鲁阿芳总是想着那座紫色的楼,凭着刘站长介绍的样子想象着它,有时做梦会梦到它。
可是,很久也没见通知来。
鲁阿芳再也忍不住了,便搭车独自进了城,终于见到了这座紫色的楼。她围着紫楼转了好几圈,觉得紫楼很像她梦中见到的模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