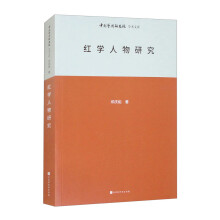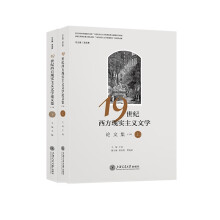《新诗“戏剧化”论说兼诗艺研究》:
三 悖论反讽和结构反讽:异质意义的并置
新诗第三种常见的反讽是悖论反讽。严格意义上,悖论的机制本来不同于一般的言语反讽。言语反讽是同一能指字面意义和内在意义的对立,悖论反讽则来自矛盾修辞,是将两个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因素放在一起,矛盾的两个方面在字面上同时出现,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溶入。悖论中的强制性组合能构成语义悖反的两级,产生对峙的张力。诗歌的悖论反讽又不仅是一种修辞,它更是诗人矛盾的情感取向、审美气质和思想意识的表现。如波德莱尔诗中便有“污秽的伟大”“崇高的卑鄙”“华美的骷髅”“美妙的折磨”等悖论反讽,表现了他对生活厌恶又沉醉的双重态度。简单说来,悖论是“似非而是”,反讽是“口非心是”。但由于悖论双方并置时互相冲突,最终必然改变了它们的字面意义,因此,悖论也具有反讽的机制。
在根本意义上,悖论是存在论反讽的典型形态。一些现代诗人既拥抱生活,但面对的又是人的矛盾、文明的悖论和存在的荒诞感这一本质真实,因此他们在诗中往往一边表达欲求、爱慕和赞美,同时又传达排斥、憎恶和诅咒,双重态度纠结在一起。在40年代,穆旦的悖论反讽深入到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环境、人性与神性等矛盾对立关系。如“因为就是在你的奖励下,/他们得到的,是耻辱,灭亡”(《神魔之争》),以“奖励”和“耻辱”相互矛盾的词语质疑了上帝对人的庇护和惩罚的双重性;又如“所有的人们生活而且幸福/快乐又繁茂,在各样的罪恶上”(《在旷野上》),“幸福”与“罪恶”的对立并置,宣布了人类原罪的悖论性存在:类似的还有“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鼠穴》),这里在“死”和“活”反复中纠结着诗人对传统的矛盾认识,一方面传统没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却又在一代代知识分子之间沿袭,这是知识分子的悖论境遇。除了穆旦,袁可嘉在诗学译介中也逐渐习得了悖论反讽,如《难民》中的“像脚下的土地,你们是必需的多余,/重重的存在只为轻轻的死去”“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词语间都是矛盾关系,把政治和难民的尖锐对立揭示得触目惊心。
当代诗人西川的悖论诗思更为错综复杂,内蕴丰富,也更具有抽象和形而上意味,并且40年代的言词悖论逐渐拓展出句群之间的悖论。他的《致敬》一诗,句群当中充满了前后之间的对立冲突。如开头写牲口的一段:“用什么样的劝说,什么样的许诺,什么样的贿赂,什么样的威胁,才能使它们安静!而它们是安静的。”这里包含一个隐喻性的悖论:牲口没有灵魂的需求,它们的聒噪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平伏的,因而诗人祈问“许诺”“威胁”给它们注入灵魂,“使它们安静”,这是存在论反讽感;但诗人还不止于此,随后突然追加“它们是安静的”,直接否定了前面所有的预设,造成了反讽意义上的悖论,由此也进一步推进了冲突。在这些悖论当中,西川传达了自己对现实经验矛盾的体验,并以戏谑的方式进行了思维悖论的游戏。
萧开愚追求语言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开启形式的栅栏、释放语义的光线”,让新的语言在经验和梦幻锻造中生成,在词语关系中生成,其中悖论关系组合就是他的拿手技艺。如21世纪以来的长诗《内地研究》,把当代发展中国的严峻生态用各种悖论修辞表达出来,语词的紧张变成了现实的紧张。“我们煮干河流和湖泊,使英雄无水浒”,公约词语被掐断关系,隐喻了人类扼断自己脖子的愚蠢;“从先进一边看,是反省的和尚拖着后腿”,先进与后腿的并置,嘲笑我们天天念叨的“先进”永远不会反省自身的盲动;“我们逐路而居,迁就道路而不使道路迁就我们”,把人造路的本末倒置揭示了出来,最终,人陷在“我们给出路捆在道路”的烂局当中。
欧阳江河的悖论修辞最有个性,他习惯用抽象语词构置智者的诡辩式悖论,将所指、经验拆卸再组装,生出新的感性诗意,同时又切中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存在困境,如“从思想的原材料/取出字和肉身,/百炼之后,钢铁变得袅娜。/黄金和废弃物一起飞翔……收藏家买鸟,因为自己成不了鸟儿。/艺术家造鸟,因为鸟即非鸟”(《凤凰》),以悖论语词写出了人难以飞翔、难获自由的沉重现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