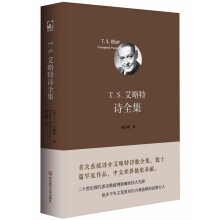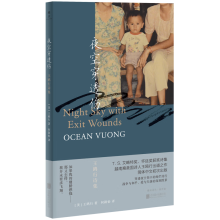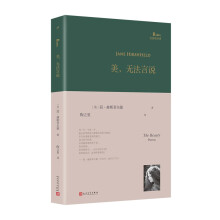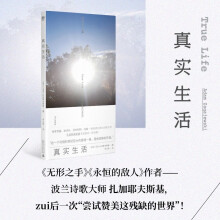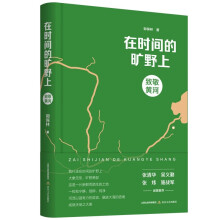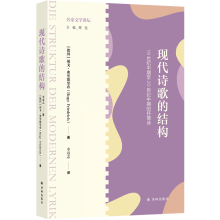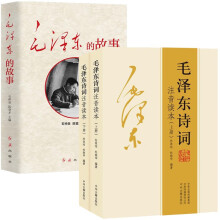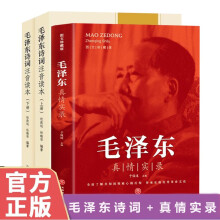《诗之为诗:<诗经>大义发微 卷一》:
至于这种”新道德“究竟是不是好道德,”新文化“究竟是不是好文化,乃至根本上是不是道德和文化,乃至是否够得上”政治“的名称,他们就不像古人那样善于反思了。因为,现代学术最崇奉的所谓理性,其实不过是激情的奴隶。所以,究竟是自称”启蒙了的、独立自主的、富于批判精神的“现代人善于理性地思考,还是古人更善于理性地思考,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会发现,虽然顾颉刚等现代学者把宋代和晚清质疑古文经学的诗学引为同类,作为他反对传统经学的武器,但实际上,顾颉刚与朱子的距离其实更远,而朱子和毛诗的距离其实近得多。虽然在解释细节上,朱、毛多有不同,但在”诗何为而作“”诗之所教者为何“等大问题上却分享共同的前提(可比照朱序与毛诗大序),这个前提便是从尧舜先王的”诗言志、歌永言“,到文武周公的”陈诗以观民风“,到孔子的”思无邪、兴观群怨“,到《礼记》的”温柔敦厚而不愚“一路而来未曾断绝的诗教传统。至于顾颉刚和朱子,虽然在解释细节上前者多利用后者,但在”何为《诗经》“”为什么读《诗经》“等根本问题上,却有着本质的分歧,乃至全然对立。
现代人批判毛诗是为了”反叛正统“,所以,他们援引宋人的时候,也把宋人打扮成”反叛正统“的先驱。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革命叙事,不宜误置于古代经学之上。历史上的诗学正统并不一直是毛诗,譬如西汉诗学的正统就是齐鲁韩今文三家诗。即使在毛诗被官方定为正统之后,也并不等于它在学理上毫无争议地成了正统。所以,古人批评毛诗并不见得是为了反叛正统,而是相反,在大多数时候恰恰是为了维护正统,譬如今文三家诗的正统,或者某种理学教化的正统。无论如何,古人并不怨恨正统、反叛正统,而只是要辨明正统、发扬正统。在现代人那里,毛诗受到质疑是因为它代表”正统“;但在古人那里,毛诗受到质疑却并不是因为它”正统“,而是因为它不够”正统“。
何为正统,在古人那里主要是根据义理和师承,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经传的正统维系于道、德、仁人师友与经义传承,而不只是文本的真实性。在古人看来,义理的不变的真实性,恰恰是要通过文章的可变的随时损益来传达和保持的。所以,孔子晚年自卫返鲁之前才感慨故乡好学的青年”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也正是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的文质相复之义,也是《周易》所谓变易不易之义。汉以来的今古文相争传统、宋以来的集注和语录互补传统、”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论战传统,都活跃在这个文与质、变与不变的关系之中。所谓”文“与”献“(即文本与师承),古人或有偏重,但却未曾偏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