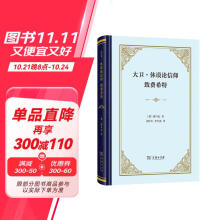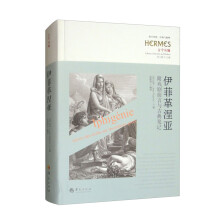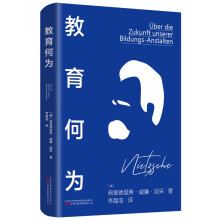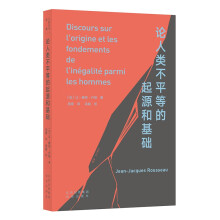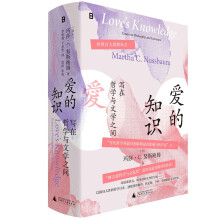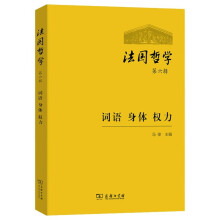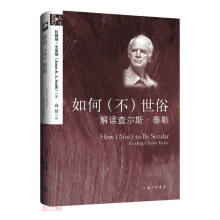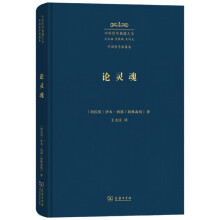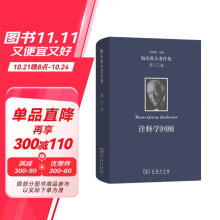《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稳定性问题研究》:
权威道德和社团道德适用于人们在具体的社会交往环境中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守,只有当人们对于其中密切交往的他人产生具体依恋,对于依恋对象的信任和情感转移到权威和社团的正义规范上,才会使人们对正义产生依赖,实现对于道德规范的遵守。如果人们处于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权威道德和社团道德就很难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人们对抽象的道德原则形成更深刻的认可,从对具体交往的依恋关系转移到抽象的具体原则的信奉,这是道德发展的更进一步要求。
道德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高阶段,是人们对抽象原则的信奉,权威人物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自己的道德原则,但是权威也有可能犯错误,当权威人物没能遵守道德规范的时候,我们对道德的坚持就主要取决于对原则本身的信守。经过权威人物和社团道德的引导,正义规范本身内化为道德主体的行为准则,前两个阶段只是认知过程逐渐深化的必经之路,而对于正义规范的内在认同,即形成对于抽象原则的正义感,才是正义稳定性的最终归宿。通过前面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一种抽象的应该、一种义务感的形成。①对于抽象的正义道德本身的感情代替对于权威、社团的依恋成为最高理想和动力,“现在他想成为一个公正的人。在这里,行为公正的观念,以及发展公正的制度的观念,慢慢对他具有了与以前那些次要的理想的类似的吸引力”②。当然,这种道德观念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爱与信任的感情培育,成为进入人们心中的情感依赖,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抽象原则超越权威和社团成为人们的最高指示,道德情感的最终形成却不能够跨越前两个阶段直接培育。
由此我们看到,正义感不是人们心中凭空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外在的道德规范的强行灌输,而是道德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根据外在道德规范对我们独立尊严价值的维护,并通过互动关系内化为个人情感。第三个阶段的心理法则可以做出如下总结:如果我们在前两个心理阶段感受到了足够的爱与信任以及尊重,那么作为满足两个正义原则的制度框架的社会合作系统的受益人来说,他将在第三个心理阶段获取稳定的正义感。①但是,当我们形成对于抽象正义原则的正义感之后,并不意味着对于社会联结的爱与信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我们承认抽象道德原则形成的正义感是更高级的正义稳定性,但是以爱与信任为基础的社会情感纽带也可能发挥着维持正义稳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于共同体主义的观念中。在共同善指导下的社会交往活动中,社会情感的归属是正义稳定性的重要来源,罗尔斯对于社会团体中同胞之间爱与信任的重视,也体现了其对共同体主义价值的重视,只是在罗尔斯看来,正义稳定性的最高标准应该是高于共同体情感纽带的正义感,成熟的道德情感的形成比起友爱与互信的情感纽带更有利于正义的稳定性,“无论如何,当存在友谊和相互信任的自然纽带时,这些道德情感比没有这些纽带时更为强烈”②。
综上所述,罗尔斯论述的正义感培育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权威阶段的榜样力量,社会团体的相互性交往,以及抽象道德原则的内化,循序渐进,从外部具体的道德榜样到内在心理的抽象原则,经历了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罗尔斯正义观念心理层面的稳定性主要是以单个的道德主体作为考察对象,主要目标是每个道德主体获取对于正义观念的认同感,核心概念是道德主体的道德情感特别是正义感,主要关注个人道德规范与正义感的形成。最终结果是理性的正义原则进入情感世界,正义原则内化为人们心中的正义感,也就是获得正义观念的内在稳定性。按照罗尔斯的论述,道德的三个阶段是形成稳定正义感的必经之路,而且一旦正义感缺失,也意味着个人三个道德发展阶段出现了问题,但是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难道整个人就不能形成稳定的正义感了吗?罗尔斯对于成年以后人们的正义纠错机制缺乏进一步的论述。同时,作为孩子培养道德规范的第一步骤,如果父母本身不是一个公正的权威,孩子们也很难形成正确的正义观念,更不用说稳定的正义感了,罗尔斯道德发展理论缺乏对于家庭内部成员正义观念形成的具体讨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