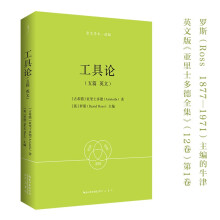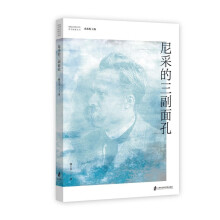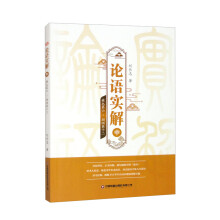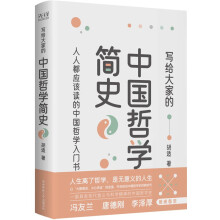印度对中国的称谓。①“内学”是佛家对佛学的自我称谓,佛家称佛教以外的学问为“外学”“世知”。成立内学院的初衷,旨在复兴在唐以后久遭冷落的唯识学(佛家认识论)。以便搭建一座方便接引注重认识论的西方知识的桥梁。后来拓展为对南北朝盛行、唐以后衰微的“毗昙”学(因缘论)、“涅椠”学(解脱观)、“般若”学(实相学)的研习。支那内学院曾经是现代中国研究佛学的重镇。
“新唯识”是熊十力在儒学基础上参以西方哲学思想,对佛学的新阐释。“唯识”,是古印度大乘佛教中瑜伽行派集中弘扬的宗教纲领。瑜伽行派以《解深密经》和《瑜伽师地论》为经典依据,以“识”为中心——佛法把心性的“了别”功能,即人的感受、认知、判断能力,称作“识”或“心识”,组织起一套概念繁多、结构复杂、逻辑绵密的义理系统,来解释世界的现象和本质。佛学史上把瑜伽行派弘扬的这一套义理,称为“唯识学”。瑜伽行派最基本的主张是“万法唯识”,认定世间一切物质存在与精神现象,从本质上说都不自足,都是心识的变现。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列宁集中批判过的贝克莱的“世界是我的感觉”。
唯识学把“识”或心识,由低到高分作三个层次八个方面。八识心田中,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待境而动,所得尽是一些唯识学称之为“现量”的倏生倏灭的直接感觉。由于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待境而动,对象性特别强,因而所得的“现量”知识,都具有倏生倏灭的“遍计执”性。第六识唤作意识,“意”,就是作念思量。唤作意识的第六识,能综合前五识所得之感觉,进行推理。故而它能超越前五识,给人以“比量”知识。所谓“比量”知识,就是用名言概念推理而得的知识。按佛家立场,第六识意识的活动,仍然有很大局限。第六识意识总是“唯外门转”,仅仅停滞在了别外境上,所得的“比量”知识,因而具有待外而足的“依他起”性,同样肤浅而虚幻。八识心田中,第七识末那识,地位很特殊。“末那”是梵音的直译。梵音“末那”,也有“意”即“思量”的意思。不过,中土宁可笨拙地音译,拒绝义译。是因为第七识的“思量”,是“恒审思量”,和第六识意识的“推理思量”有个本质区别。第六识的综合推理,是“唯外门转”,仅仅停滞于了别外境,不自反省。第七识的“恒审思量”,是“内外门转”,即不止了别外境,还在“内门转”,批判性地“思量”前六识以及前六识之所得。因而,“恒审思量”的第七识,能了别世界的本质,不是前五识感觉中呈现出来的模样:“山就是山,水就是水”,也不是第六识“比量”推理给出的认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从而为破除邪执、通向“真如”提供了方便——“真如”是佛家对他们要体证的“最高真实”“终极真理”的称谓。第七识末那识虽然能了别“真如”即世界的本质不是前五识直观感受到、第六识推理思量出的那个模样,但它自身还不能体证真如,即还不能了别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第七识之所得,仍属“非量”——不如实的思量判断。唯识学把第八识阿赖耶识,称作八识心田中的“心体”“心王”。“体”是“本体”,即本根本原;“王”是“帝王”,即最高统帅。称阿赖耶识为“心体”,是因为依唯识学,第八识阿赖耶识中储存着前七识的“种子”,有它,才可能有前七识的活动。第八识阿赖耶识是前七识之“本体”,前七识的活动,是第八识阿赖耶识遇缘而显现出的“现行”之用。“现行”是与“种子”相对应的佛学概念。“现”谓显现,“行”谓活动——主要指前七识的现前活动。种子潜藏,现行发显。称阿赖耶识为“心王”,是因为第八识不仅能“证自证”,反省自身,体证真如,而且还能像贤君圣王一样,正确统率前七识,透析前七识认识之妄,“转识成智”,把前七识所得之“现量”“比量”“非量”,转化成“真现量”“真比量”,使之成为体征真如的借助。因而第八识之所得,才具有“圆成实”性。由于此派主张“识有境无”,故而佛教史称之为“有宗”,以区别于大乘佛教中主张“诸法性空”的“空宗”。
唯识古学,南北朝时由菩提流支等西来和尚译介到中土,但其间有一系列问题隐而待明、微而难化,难以满足中土人士求法之心。唐贞观年间,玄奘西行求法,从古印度戒贤处得唯识今学真传。归国后集中弘扬,创法相唯识宗。一时法席甚盛,东传高丽、日本。由于唯识学结构复杂、事数繁多、逻辑严密,宗风与正在兴起的务求简易的禅宗正好相反。故而法相唯识宗再传至窥基①,窥基著述宏丰,尚能光大门楣。窥基之后,传承迅速式微。不过,由于法相唯识宗特别关心佛法认识论,而认识论又是中国本土思想中的薄弱部分,故而,中土思想界、佛学界对法相唯识之学感兴趣者,历代不绝其人。“清初三大家”里的王夫之,就对唯识学深感兴趣,著有《相宗络索》。20世纪初,太虚、欧阳竞无、唐大圆等,以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为依托,发愿复兴唯识学。吕潋曾任支那内学院教习、教务长、院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