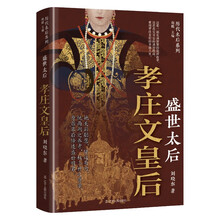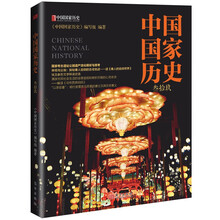《心殇 我的乳名九一八》:
一、“九一八”打破了满族村的宁静 根据老人讲,在我出生的前一天,即1931年9月17日,已是金秋时节。我的老家在沈阳市郊区杨千户屯。这个小村子东有岗,南有岭;在岗岭之间,从东南向西北流淌一条小河。它的东侧,因处在秋收的准备期,村里村外都很宁静。岗地和平原的五谷,正在争彩斗艳:大豆一片黄褐,如沙似毯;高粱枯绿的波浪泛着鲜红的泡沫;玉米一棵棵如同抱着红发娃娃的村妇在闲聊;水稻生在最低处,对周围近邻,为了显示自己生长的不凡,每年这时都脱去轻飘飘的绿纱,换上沉重带格子的黄袍…… 老农们,大都在自家向年轻人安排完收割事务,慢步走到各自的田间地头儿,远望近查,咧嘴眯眼,笑出一脸皱纹儿;有的还哼起了皮影戏曲…… 与大地的多彩比较,天空似乎单调得多。不过天蓝得像海水般透明;云白得像棉糖一样馋人;因之更让人仰望不止,环视不停。再加上母燕带领仔燕学练飞翔,学累了一齐落在低空的电线上,如同一串会唱的珍珠。这更为蓝天增添了几分活气。
顺着从东岗南侧流来的弯曲小河,走进杨千户屯:房屋稀稀落落,排列无序。东南部的砖墙大院里住着大财主;西北部用土墙围起的大草房中,住着小财主;三间草房被秫秸障子围的小院中有牲口棚和大车,不算财主也不是穷人家;那一片高低不同,忽前忽后,朝向不定,有起脊草房,有无脊平房,乃至不成房屋的“窝棚”,才是穷苦的农民住所。因为这村有一半左右“满(读阴平)洲”人,穷富都很讲卫生,注重礼节,所以每个秋收大忙之前,几乎家家妇女都干着同一件事:洗、浆、锤衣物。“洗”,即是一年一次地拆洗被褥和平日不常穿的单夹旗袍;“浆”,即用面粉熬制成糨糊,稀释后把洗净的衣物放盆里搓揉匀乎后,抖掉糨糊颗粒,晒干;“锤”,把浆好的衣物晾干后再用水喷潮,抻平褶皱,叠好,放在一块二尺来长一尺来宽的“锤衣板”或“锤衣石”上,用两个镟得光圆的棒槌,像敲鼓似的仔细锤打,直到衣物平光无褶为止——如同现在用熨斗(或烙铁)熨烙的一样。这么浆锤的好处:一般说,是看着干硬平整,穿着棱是棱角是角;但对贫苦人家,还有掩盖破旧和耐用的好处。因为穿用快破了的衣物,用糨糊浆后锤完,跟新做的一样平整光鲜;而且抗抻耐磨,脏后易洗。
由于这种活计都是在同一时节进行,因之村村都棒槌声声,近处的“乓乓乓……”远处的“哒哒哒……”强弱不同,快慢有别;木板石板声混杂,更叫人感到近听如敲鼓,远听似打板儿。因为这声音能使人从中体味出村妇的勤劳、爱整洁及其锤衣人灵柔的动式,和自足的笑容,本地人都不嫌吵闹。外地人走在村路上听到,也常驻足细听,因之越发感到风微气爽,天蓝云白,五谷飘香…… 在这个犁形的小村的北部西侧,在周长200多米的大水泡子北岸,有所孤单单的三间起脊的草房;院子被规整的秫秸障子围住;从朝南开的院门可见院内土地干干净净,农具摆放得规规矩矩;门外左侧卧着一条黑色大狗,盯盯看着泡子旁扒食的几只小鸡和水面上的鸭鹅——好像在主人安排下为鸡鸭放哨。屋里同样传出木质锤板的响声…… 这家显然属于可以自给的下等“满洲”农家,姓胡——就是我们家。据《家谱》记载:上十代祖先胡善友,是1627年随皇太极迁入盛京(今沈阳)的正黄旗官员,逝世后葬于专建庞大的陵园;约五代后,随着清帝逐渐衰腐,我家的文武官员也日落西山了。我祖父是清代最后一批秀才,之后一直当塾师;其弟兄有的从政有的搞经济,都比我们这一支富裕。我父老大,自幼勤劳,帮老人供两个弟弟读书立业,自己一天书未念,却因偷听老父讲课,自学到能看书、记账程度。二叔胡万朋,字承烈,当时在东北军驻北大营当炮兵团长;其家属住在邻村。因为家底特薄,子女多,我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也只有大哥振五读过书,后到北大营当兵,已升为士官。当时大姐已出阁;家里只剩两个姐姐,一个15岁,一个12岁;两个哥哥,一个9岁,一个3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