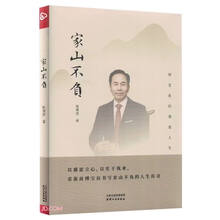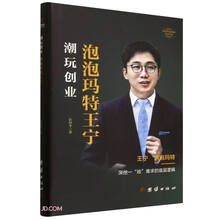《五年,高管养成记:通往“捷径”的自传》:
我不说,或许没人能猜到我曾经在三所大学任职过。
我在师范体系中摸爬滚打了10年,从师范高中到师范大学,从17岁花季少女到27岁花样年华。“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八个大字像“毒瘤”一般生在了我的心里,长在了我的骨髓里,发酵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研究生毕业了,我有且只有一个选择——当老师。
记得毕业前半年,经熟人推荐,我在东北某高校AC学院中文系担任实习讲师,主讲大四毕业生的选修课。由于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研期间主修“中国明清小说研究”,我本人又对古典文学中的“狐鬼神妖”特别感兴趣,因此我独创了一门选修课(该课程花了近一年时间来撰写课件,课件达100多页)——中国狐文化之《聊斋志异》中的众狐分析。
那年我二十几岁,下面的大四学生比我最多小三到四岁,他们马上要外出实习找工作,这门课是选修课,选修课就意味着可选可不选,可上可不上。对于我这个还没毕业的实习讲师而言,他们应该是很不屑且对我的课没抱什么希望的,但是我还是认认真真地备了课,哪怕有一个学生在听,我也要在讲台讲到最后一分钟,就为了对得起“教师”这两个字。
如果没记错,一共六个班级听我的课,上午四个,下午两个;如果没记错,从我第一次上课到最后一次结课,基本上没有学生缺课(病假除外);如果没记错,第一节课开课时我曾经对大家说,“如果觉得我讲得不好就别来浪费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留下来听了,请遵守我的规矩”,结果,到了下节课,人更多了;如果没记错,这门课六个班的学生没有一个挂科的,且成绩优秀的占多数;如果没记错,这些学生如今应该大多像我一样,已成家立业,有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浮躁的大四学生几乎座无虚席地听我讲课?听他们的班主任说,其他教授的课满座率也没这么高。到底是我还是“狐”迷住了这些记得学期中间一次课上,在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几个中文系老师走进了教室,坐到了教室一角,起初我以为他们是检查学生出勤率的,可过了20分钟还没走,有的老师还在记笔记,我知道了,我被听课了。
听课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例行的(此次显然不是,例行的会提前通知),一种是突袭的(突袭的肯定有情况,不是有人举报你讲得太“好”就是讲得太差)。那时候的我,太年轻,当脑子快速闪过这些念头的时候,是有点忐忑的。不过“既来之,则安之",我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反正我也没传播有损党国的反动言论,没什么好怕的(其实心里还是怕怕的)。
《聊斋志异》中有很多关于“狐”与人的两性描写,那节课要讨论的正好就是关于这个的尴尬话题。
如果没人听课,我肯定按照自己的节奏展开,因为我的研究生老师曾经在课上讲诸如这些内容时,在座的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丝毫没有肮脏感——这是文学,也是美学,更是哲学。今天,有几个老教师听课,我是有点犯怵的,我讲还是不讲?不讲,感觉蜻蜓点水没说透,好像有悖职业道德;讲了,估计我就惹“事”了,“事”小要解释检讨,“事”大估计得请我走。
关键是我没时间过多思考,你说我到底讲还是不讲?是的,我还是讲了,不讲肯定不是我的风格,不仅讲了,还讲得“天花乱坠”“口吐莲花”。好在课上没一个睡觉的,没一个看手机的,没一个开小差的,四个班的学生,分小组讨论得热火朝天,辩论得相当激烈,最后大家对这些所谓的“性描写”的社会学含义与文学含义在分歧中达成了一致,这样的课程让老师与学生都很兴奋,这些敏感话题的热烈探讨有一种很文青的感觉,仿佛革命斗土完成了反帝反封建。
我估计大家可能比较关心那些老师的反应,说实话,我也特别关心,可是当时没时间看他们的“脸色”,因为场面太热烈,思维太活跃,我几乎已经忘记还有几个“老家伙”。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