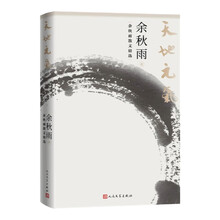未圆湖
世事难有圆满,为什么又要圆满。
大学站的某一个出口,有一个很像自由女神像的自由女神像,穿着彩虹布的裙子。你绕过她往树林的深处走,你就会看到那个大池塘。
出错了口,你只会看到很多的士,大巴,小巴,它们把教授们带往马鞍山,他们喜欢马鞍山。如果他们不住在学校,他们便住在马鞍山。
如果你已经出错了口,你看到了鸿福堂,你就在美心旁边的通道左转,你仍然回得到大学,沿着沉香树围起来的小路往上走,上面有博物馆,图书馆,所有的一切。
杨美丽离开了以后,我不再去那所大学。我们去过的那个教工食堂,我都忘记了。楼外面开满了木芙蓉,或者金合欢?全部忘记了。
我会走去那个池塘,大学站出来,只要走三分钟就是。不再有人在那里等我,也不再有人坐在我的旁边,路旁全是树,金黄色的树叶。杨美丽说过的那些话,我也忘记了。她有一颗美人痣,我只记得这个了。
池塘的周围经常有很多人,拍鸟的人,拍青蛙的人。他们有望远镜也有好相机。我的相机落在哈德逊河里了,我的望远镜曾经看得到月亮表面的沟壑,离开美国的时候它被送给大山,大山也离开美国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也一定没有那台望远镜的下落。大山离婚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爱情。
我两手空空地走过那些人,池塘里有枯败的荷叶,他们在拍它们。死了很久白肚皮朝天的腐烂乌龟,他们在拍它们。
众志堂的早餐简陋,出前一丁加两文。收银的阿姨捞面条的阿姨越来越不高兴了,她们都希望自己隐秘地藏在池塘的后面,永远。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去那里了,他们全部说普通话。
每隔五年,中文大学会有诗歌的夜,那一夜,诗神们会去那里。他们的后面,已经没有神了。凡人也不追随神了,凡人追随自己的欲望。
如果我还有一些故人,每隔五年,我会见到他们一次。其实我从没有爱过他们,我嫉妒他们,你怎么会去爱自己嫉妒的人呢?你甚至不会去爱神,人一直都是嫉妒神的。
还有追随乐队的女孩吗?她们洗所有的衣服,争风吃醋,她们搭大巴士绕过半个美国,她们的胸口文了谁的名字。我一直以为她们跟追随诗人的女孩们不一样,也许追随诗人的女孩更高贵。也许她们都一样。
这些女孩全部灭绝了。
有些神从来不知道自己是神,是你们把他们推举为神的。人亲近神的目的没有人知道,成为神,或者受神的喜爱,最终还是会成为神?如果有人说我也曾经是女神,好吧没有人知道。
他很安静地说过,你有一张孩子的脸。他说再过十年,你的脸都不会变。可是他没有认出我来,真的是十年了。他那么老了,我那么爱过他。
舞台上有人用广东话朗诵,他太坏了。可是我们不都一样吗,独特令你成功,每个人都独特,越来越独特了,大家不再是一张脸了,这个世界。
我问他借了一支笔。隔了好多年,我问他,还你了吗?他讲没有,其实我还给他了。他忘记了。
杨美丽去顺德买了家具,那些家具直接运去了美国,它们摆在美国的客厅里,庞大又美丽。她们都去顺德买家具,所有暂时离开美国的女人,她们只是出来转一圈,买几件顺德家具。
露比也会有那么一天,也许是明天。她不再来中文大学了,她也没有时间看贾樟柯的电影。那个夜晚我和露比在一起,她为什么要戴一条巴宝莉的围巾呢,是寒冷吗?全部忘记了。
这一个五年的夜晚,我没有再去中大。那里更热闹了更冷清了,新的人旧的人,都与我无关了。有一些早晨,我还会去那个池塘,他们叫它未圆湖,白色的鸟在湖面徘徊,鱼都太大了。
我仍然想得起来金门桥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挂满了日本画的房间,每一幅画都是圆,大的小的圆,长的扁的圆,浓的淡的圆,他们说它们顿悟,虚无、空或者圆满。我拿起一支笔,纸是灰暗的,我不知道我的圆圆不圆,因为它很快便消失不见,于是我画了第二个圆,它们都不见了。
世事难有圆满,为什么又要圆满。
金牛星座
当你只是索取时,爱从来都不够。从来都——不够。
我离开以后,人们遗忘我,我的MSN只剩下三个人,她是其中之一。有一年春天她说她也许结婚,我给了她祝贺,第二天她说不结了。她的失去特别突然,我给她寄了水莲香水,可是香水不是男朋友,她那三天一定过得艰难。夏天我从香港打电话给她,我说我现在很空,如果你需要我去中环问那个男人为什么。她说不要了,她说忘了吧,她说我忘了,你也应该忘掉。然后她说你和比尔一起吃饭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和比尔一起吃饭。她说也是,比尔那样的男人只是用来观赏的。
后来我在香港公园看到比尔,我以为我会看走眼,我托着下巴把比尔从头到脚看了一分钟,这一分钟里,他吃了柚子沙拉里的柚子。
这个人温柔又有礼貌,可是一点温度都没有。
没有一个男神是从一开始就是男神的。他起初也会惊讶,直到习惯到厌恶。如果光环闪亮又强硬,最好欣然接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