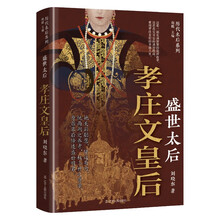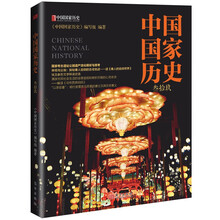然则此《新国语》五十四篇何为而来?其书与《左氏传》究竟有无关系?关系如何?是皆应有合理之解释者。《新国语》今虽不存,然就汉儒习尚及刘向所序《新序》、《说苑》测之,亦自有说:
(一)《新国语》较《国语》增多三十三篇(钱穆因《战国策》恰为三十三篇,并《国语》二十一篇合而成五十四篇,谓为《新国语》。诞妄实甚,无征不信)。意者刘向因秘府原《国语》残缺不完,乃于校理群书中留意搜辑有关春秋时代各国史文,以补旧本《国语》之不足。如孔衍撰《春秋后国语》,方以类聚(见《史通》)然。比于旧《国语》,无国者或增其国;有国者或增其篇;有篇者或增其段,故篇幅增多倍于旧,几与后来之《左氏传》分量相等。以是可知《新国语》必为《左氏传》所取材,其材料较旧《国语》丰富故也。
(二)刘向“分”旧《国语》为《新国语》,当由于旧《国语》原分配之不适当。如今本《郑语》,当还《周语》,向根据内容,另自分类,犹班志于《七略》之分类颇有出入是也。因是《新国语》比于旧《国语》,或去其重复,如文公请隧,阳人不服,《周语》、《晋语》两载,应避其复;或易其次序,如《晋语四》末章文公即位二年云云,不当在末尾,应调整其次序。入者出之,出者入之,所以《汉志》注不言刘向“着”而言刘向“分”者,盖由于此。后之《左氏传》隶事准确,极少谬误,则《新国语》固已为之奠基矣。今观《汉志》,儒家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有《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而刘向本传云:向“采取诗书所载……次序为《列女传》……及采传记行事,着《新序》、《说苑》。”惟向所作《列女传。叙录》但云:“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初学记》卷二十五,《御览》卷七百一引)《说苑,叙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除去与《新序》复重者”(见宋本《说苑》及《全汉文》卷三十七),可见《列女传》、《新序》、《说苑》三书均非刘向之创作;而为当时所存旧籍,刘向因其次序浚乱,加以整理排比,除去重复,种类相从,间或采取传记行事,加以补充。然则刘向此法,岂非其“分”旧《国语》为《新国语》一有力之旁证乎?夫《左氏传》既采《新序》、《说苑》、《列女传》之材料而另加以组织,或易其字句,则其取材于《新国语》,亦可类而推也。
至于《新国语》之亡佚,其时当在班固之后。因《汉志》虽本《七略》,凡有出入及有录无书者,班氏皆有注说明。《新国语》既见于班志,又无“有录无书”之注,何能凭空捏指刘歆“既取《国语》。为《左氏传》,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如康有为之说。况新、旧《国语》,内容及编制皆不同,本无碍其共存。至如《左氏传》,其内容及编制,更与新、旧《国语》有别,宜其更可共存,歆又何必灭其迹?孙海波深知“汉儒习尚,喜掇拾遗事,分析篇章,托之往古,或损益古籍,参附己意,易以新名,初无作伪之意,如刘向《说苑》、《新序》之类皆是也。”斯为平正通达之论。孙又云:“歆既见《国语》事多与《春秋》相发明,因取以解经.而易其名曰《左氏传》。复罔罗旧章,为今《国语》二十一篇,以承其旧,别为《新国语》五十四篇之名,以乱其真。”如此,则又将《新国语》一书,置于“汉儒习尚”之外矣。且解经非易事也,乃谓“因取(《国语》事)以解经,而易其名曰《左氏傅》”,则歆之低能取便亦已甚矣,岂其然乎!孙氏于刘歆之才之学估价过低,至谓“刘歆之徒,不若史迁之才之美”,因之其于《史记》及《左传》在中国文化历史发展中之地位及其影响,不免颠倒其先后之关系,其失也与吾国自来学者同。此盖见欺于刘歆而不察。今以历史发展规律观之,《史记》及《左传》之先后关系,庶几得其正也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