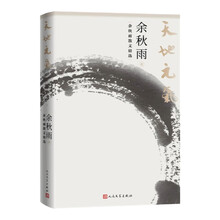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第四等爱情: 旖旎风情不知出自谁手》:
尘埃落满 寂寞花开
我遇见你,我记得你,这座城市天生就适合恋爱,你天生就适合我的灵魂。
——杜拉斯上海名作家程乃珊母亲与张爱玲曾是同学,就读上海圣约翰贵族名校,她母亲说:“张爱玲并不起眼,不和人来往,不说话,又瘦又高,人缘不好,很多人排斥她,总是独来独往。”“张爱玲成名了,亦不和人来往,一生的朋友,只有一个叫炎樱的黑胖女孩子,两个人是看一眼就天地洞开的那种,就连她的婚姻,也只有炎樱在场。”这段回忆可信度非常高。1936年夏,在高中二年级班级合影中,张爱玲立于后排,身着暗色旗袍,体形单薄,落落寡合。1937年的高中毕业照中,很多女同学烫了新潮卷发,穿得花团锦簇,张爱玲依然立于后排,仍是一袭式样陈旧的深色旗袍,神情萧索。
多年以后,张爱玲自己在《小团圆》里也是这般描述自己:“九莉只会煮饭,担任买菜。这天晚上在月下去买蟹壳黄,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卷的长发。烧饼摊上的山东人不免多看了她两眼,摸不清是什么路数。归途明月当头,她不禁一阵空虚。二十二岁了,写爱情故事,但是从来没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
“九莉戴着淡黄边眼镜,鲜荔枝一样半透明的清水脸,只搽着桃红唇膏,半卷的头发蛛丝一样细而不黑,无力地堆在肩上,穿着件喇叭袖孔雀蓝宁绸棉袍,整个人看上去有点怪,见了人也还是有点僵,也不大有人跟她说话。”即便是高度写实,依然透露出典型的张爱玲式的矜持,她在没有恋爱前真是寂寞,难怪胡兰成要称她为临水照花人。一个人要度过这么漫长的尖刻、孤独、没人缘的一生,简直比她的小说更传奇。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金锁记》写道:“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如果不是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这篇小说刊在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时任汪精卫组阁政府的文化官员胡兰成躺在庭院的藤椅上漫不经心地翻阅,骤然读到,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读了一遍又一遍。
摇曳多姿的文字,满纸氤氲的烟华,令胡兰成无从忘怀,他向苏青要了张爱玲的联络方式,想要去拜访她。
那时的胡兰成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总有人评述这段情事,以为他们的相遇好似朵朵饱满的孢子植物喷薄而出,从悲伤的原点出发,走向的是广阔的虚无。
却不知,世间万事万物皆有自己的命运,没有人可以抽离前尘往事,知悉遥不可及的未来。他与她,是芸芸众生还在追求今生今世时一块岩石与另一块岩石定下的死生契阔。亦是男女在天下人面前相悦,这样坦荡,又这样私情。情怀可以是这样媚,然而又真的是无情。他和她,是风流事,亦是家事,更是没有事,总总都是物心人意的珍重。
就像张爱玲未曾写完的《少帅》。在这部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为原型的作品里,少帅去了河南前线,赵四小姐和朋友过中秋节,她当然想念他,“两人走在电车铁轨上,直到一辆电车冲她们直压过来,整座房子一样大,当当响着铃,听上去仿佛是我找到的人最好,最好,最好,最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