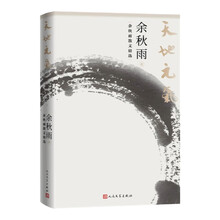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遥远的,不回头的 : 边芹散文精选/本色文丛》:
痕迹
先人去了哪里?自从“科学”统领了游兵散将的人生观,“进步”就把古往今来谁都未能绑架的历史驯服了,从此这头穿云过雨的巨兽接到各方邀请,上至太空下至地底,却再也没有选择方向的随意。历史方向没有了悬念,就像再也没有惊喜的旅行,让途中人惆怅。那日在玄武湖边闲步,经郭公墩,读了几首郭璞的《游仙诗》,便觉两千年前做鬼也幸,虽行不至万里,飞不过山尖,但满脑子旅行终点的惊艳。
如果以“出入”二字概括人生这或长或短的过程,“人”不管多么卑微,“出”都是拖泥带水的,仿佛曾经的每一步都预谋着要留痕迹。那些魂灵去了哪里,我们终究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能在他们停靠某个站点的时候,依稀地窥到旧影,但那已经不是鲜活的影子,而是追着魂灵游历世纪的器物。
某日我走进一间展室,巴黎古董廊一个半营销半展览的陈物室,里面一房间抽鸦片的器具,集一个半世纪中国各地工艺之大全。这个星球上可以搜罗到的金石土木,经手的灵动、审美的智慧,以惊世骇俗的别样和精致,化作令人眼花缭乱的瓶瓶罐罐,众星捧月般围绕着主角的主角:烟枪。
谁能想到一个民族沉落的影子会这样精雕细琢地跨越世纪,凝缩成足以与时间抗拒、与生命唱反调的物品,从一个个主人的手里滑脱,惊魂似的尽可能抹去血迹和苦痛,将被剥去的尊严收藏在灵巧的指缝间,悄悄地逃出命运之门,幻变为抽象的唯美,聚会在一间灯影迷离的展室里。那就像金碧残留的大宅云集了上流社会的遗老孤少,一屋子脂粉香绢,隐愁暗限、离泪别梦全都梳理成册,入了戏。
从那一天起,我意识到“出”并不是无踪无影地走脱、灵山仙水地化烟成雾,或者撕心裂肺、血荐轩辕地走进文字、彪炳汗青,“出”的全部意义在“留”。为此先人们可谓绞尽脑汁,从墓葬习俗到石刻碑文,华夏先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透彻地悟到去与留之秘密关系的人,由此不必依附于神、托付于主,是那份“留”的殷切、贪婪和固执坚守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千代万世地见证着我们的文明。传承和记忆时常没有想象的虚幻,亦没有文字的浪漫,而是带着器物的真与实。先人用过的器物即便体无完肤也以残缺的执着携带着不弃不离的记忆,一步步跟着我们。
自古,代与代之间是靠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器物手传手牵拉的,生死相随的它们时常比血缘还要忠实,不偏不倚对抗着时间这随时随地要捅上一刀的刽子手,锲而不舍追随着突变逃离的基因,忠于职守黏合着破裂隐遁的情感,让短暂变成持久,让中止变为延续,让无情变作有情。那乌亮的竹木、幽幽反光的铜铁、拒绝时间留痕的陶瓷、永远藏着逝者体温的丝帛,替代了不知所终的魂灵,默默地守护后人。是手传手让那些被动的、没有生命的存在充满了言语;让走不进历史,也挤不进家族血缘史的它们成了历史、家族史最忠诚无误的证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