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记》成为经典
随着汉朝土崩瓦解,三国时代到来,《汉书》的尊崇地位受到冲击,《史记》却因此毫无障碍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声誉日隆。
首先,在魏晋南北朝学者眼中,《史记》不再是“谤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有如下记载。
帝又问曰:“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
魏明帝受到汉代人评价《史记》的影响,也认为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十分可恶。大臣王肃听了,立刻纠正他说:“司马迁写《史记》,不过是秉笔直书,并没有故意诋毁汉武帝的意思。倒是汉武帝小心眼儿,觉得《史记》里的《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不合自己的胃口,就删削毁弃,致使《史记》残缺不全,后来又借李陵事件报复司马迁,害他身遭极刑。所以说,心怀怨恨的人是汉武帝,而不是司马迁。”王肃的解释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但至少,他为司马迁和《史记》翻案的态度是鲜明的。
稍后,南朝刘宋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也反驳了以《史记》为“谤书”的说法:“史迁纪传,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裴松之同样认为,秉笔直书本来就是记录史实应当遵循的原则,司马迁没有隐讳汉武帝的过错,并无不妥,而以王允为代表的一些人说汉武帝应该杀掉司马迁,这种看法也太没见识了。
其次,东汉时期,官方有意推尊《汉书》、贬低《史记》,到魏晋时期,这种格局有所改变,甚至颠倒过来。譬如,西晋学者傅玄从人品上比较班固和司马迁说:“班固《汉书》,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异马迁也。”(《傅子》)《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完成的著作,这在《太史公自序》里是有所说明的;《汉书》也是班彪、班固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但班固在书中却对父亲的功劳只字不提。傅玄认为,仅凭这一点,班固就和司马迁存在很大差距,连做人都成问题,书又怎么能写好呢?
《晋书》卷六十则记载了另一位西晋学者张辅对班固和司马迁的评价: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 也。
张辅说,司马迁比班固强的地方有三处:第l,《史记》叙述三千年历史只用了五十万字,《汉书》叙述两百年历史却用了八十万字,可见《史记》精简,《汉书》啰唆。第二,一些无关于惩恶扬善的小事,司马迁不予记载,班固却都记下来,说明班固不如司马迁懂得取舍。第三,班固在《汉书》中诋毁西汉文景时期的政治家晁错,有伤忠臣之道,司马迁不会做这样的事。此外,司马迁作《史记》是首创,班固作《汉书》是因循,难易不同。司马迁又在《史记》中表现出高超的文采,所谓该平实的地方平实、该潇洒的地方潇洒,的确是良史之才。
这种褒扬司马迁、贬抑班固的思潮,自魏晋兴起,影响深远。到宋代,学者郑樵甚至在《通志•总叙》里直接说:
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如此人材,将何著述……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
郑樵这个评价毫不留情,“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的比喻也堪称经典。班固当初一定没有想到,千载之下,自己会遭到如此差评:“全无学术,专事剽窃”——汉高祖至汉武帝一段剽窃司马迁,汉昭帝至汉平帝一段剽窃贾逵、刘歆,还有一些是妹妹班昭的作品,班固自己原创的篇章实在很少,恐怕就只有《古今人表》吧。
《史记》地位抬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注解它的著作不断涌现。从魏晋至隋唐,学者研究和注解《史记》蔚然成风,见于《隋书》及新旧《唐书》记载的就有十余家。这些注解作品中,流传至今的有三部,被称为“《史记》三家注”,分别是南朝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裴骃是裴松之的儿子,有着深厚的史学底蕴。他以汉晋时代的《史记》注说成果为基础,博采经、史、子诸书,对《史记》进行集注,所以叫作“集解”。裴骃的集解详于先秦而略于西汉,引用前人旧注,一律说明,严谨不苟。他遵守汉儒“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旧例,对《史记》原文有疑问时,只客观征引其他学者的意见,自己并不妄下断语。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与裴骃《史记集解》的风格不同,他以裴骃《集解》为底本,既注释《史记》原文,又注释裴骃《集解》,打破“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旧例,直接对《史记》原文中的疑问进行论断,并对裴骃《集解》予以驳正。司马贞还在《史记》每篇结尾撰写“索隐述赞”,表现出一定文学才华。张守节生活的时代稍晚于司马贞,他花费三十余年精力撰作《史记正义》,体例仿照《史记索隐》,既为《史记》原文作注释,又为《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作疏正。《史记正义》的特点是详于历史地理,凡《集解》《索隐》未注、或错注、或注而不详的地名,《正义》都做了补充和辨正。
“《史记》三家注”各有所长。《集解》长于旁征博引、校订文字;《索隐》长于探幽发微、辨正讹误;《正义》则长于历史地理。这三部书初各自有单行本,到北宋年间才合刻在一起,并且依次分散到《史记》原文之下,成为《史记》“三家注本”。
注释作品的大量出现,说明《史记》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当然,以“三家注”为代表的学者主要是将《史记》奉为“史学经典”,事实上,在唐代,《史记》也同时成了一部“文学经典”。
唐代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积极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华而不实的骈俪文风,以《史记》为两汉古文的优秀范本,从而奠定了《史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柳宗元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文家对《史记》文学的高度赞赏。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 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传》《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退之所敬者,子长、子云。(《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退之”是韩愈的字。论两汉古文,柳宗元认为韩愈只服两个人——司马迁和扬雄。扬雄本来就是辞赋家,司马迁却没有刻意研究过文学,而在韩愈看来,他的文学成就只在扬雄之上、不在扬雄之下,可见推崇备至。那么,《史记》的文学究竟好在哪里呢?柳宗元用一个字概括,叫作“洁”;用两个字概括,叫作“峻洁”。也就是说,《史记》的文字干净、凝练、风骨卓然,简约而不简单。这是司马迁做文的风格,也是司马迁做人的境界。“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文章以德行为本,德行以真诚为先。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之志,秉笔直书,爱憎分明,非怀抱真诚者不能为之。也正因如此,《史记》才高山仰止,千古独步,成就了史学与文学的双重绝唱。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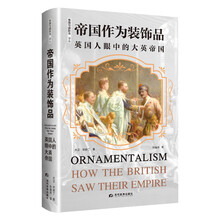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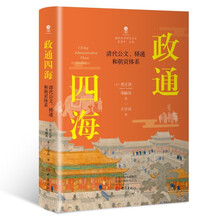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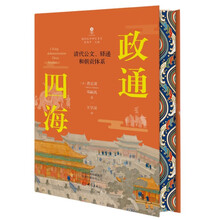

与古代经典有关的知识读物,多数是平庸的流俗之作。当你走进一家书店,或是浏览购物网站,挑选古代经典读物时,诗文选本、古籍白话译本以及那些散发着恶俗趣味的“经典中的某某智慧”一类的书,是常见的。前面所列的各种读物质量,按其顺序来说,则是每况愈下。
诗文选本古代就有,具代表性的自然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隋唐之后,它成为古人学习诗文写作的基础书籍之一。后来,它还形成了“《文选》学”这样的专门学问。直到今天,《文选》研究仍是唐以前文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唐代的《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等,是当时的人编选的唐诗读本,并一直流传到今天。明清以来,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书籍制作的技术门槛和成本越来越低,以儿童启蒙或科举应试为目的的诗文选本开始大量出现。为我们熟知的就是《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20世纪50年代之后,为适应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一些学问大家都曾编选过诗文选本,如余冠英的《诗经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等。这些书选目精当,注释简明,且断语清通,可以说是新时代的经典选本。近二十年以来,电子技术的进步使得制作一本书越来越容易,各种临时拼凑的诗文选本大量出现。虽然编选注释者多是专业学者,甚至不乏名家,但是编选诗文不属于专业的学术研究,因此学者们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此类书籍即便每年都有新产品面世,但其质量却令人堪忧。
古籍的白话译本在今天看来已是奇葩。它们也是适应新中国文化普及工作而逐渐出现的读物。对于只具备初步文字阅读能力的读者来说,这些译本是他们了解古籍内容的便捷途径。因此直到今天,这类图书仍然被大量印刷。但是,当代人大多受过古文阅读的训练,借助注释,绝大多数的古籍是可以读通的。古文自有其独特的韵味,我们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体会汉语的韵律与美感,甚至可以怀想古人的辞气、心态、日常生活乃至时代风习。但古文一经白话翻译,那些文字中的美感和灵性便荡然无存了。这就如同把新鲜的水果制成维生素片,那些天然的果香是加工过程中先失掉的东西。即使优秀的白话译者,也不能传递原始文字的美与韵。我们阅读这类书籍,就好像吃他人咀嚼过的食物,美食的滋味和入口的快感,恐怕只存在于译者的齿间。当然,翻译不能略过任何细节,因此,若我们将白话翻译当作阅读古文的辅助材料,把它们当作更加详细的注释来使用的话,这类书还是有不被卖做废纸的理由的。
“经典”中的某某智慧一类的读物,甚至不能被称作书,因为我们不能亵渎“书”这个词。《孙子兵法》与《三国演义》是被这类读物糟践厉害的两部古书。对于这类读物,实在没有评论的必要。
读书当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诗文选和译注一类的书,是文句和内容层面的通俗化,只提供了基本的阅读对象,却极少涉及古代文献的成书、流传与思想史背景等问题,这对于那些富于探索兴趣的读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这样的书见得多了,很容易让人降低阅读的期待,因为不用翻开,就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了。
那么,如何来满足读者的探索兴趣呢?我想,凡是具有此种兴趣的人,都会被学术问题吸引。但专业的学术研究与通俗的阅读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陈寅恪的《金明馆丛稿》、余嘉锡的《古书通例》等著作,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弥漫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洞见与魅力,让他们反复玩赏,三月不知肉味。但这些著作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显得过于艰深了。学术研究充满了无穷的魅力,但专业的书写方式成了一般读者了解学术问题的障碍。因此,在一般层面的阅读世界里,缺少的正是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有趣学术问题的书。
“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独辟蹊径,将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有趣问题,以通俗化的语言讲述出来,成为一套让我们知其所以然的书。
在这一套书里,经典的成书、文本、思想与流传成了主要内容,这些也是专业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非常专业的青年学者,她(他)们经历了良好学术训练,对前沿问题有敏锐的嗅觉。当她(他)们想把那些有趣而精深的问题,用清通的语言写出来时,我们真该庆幸,同时也当感谢她(他)们。因为这样一来,学术就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狂欢了,而是可以惠及众人,让许多抱有文化情怀的读者所熟知,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和探索学术研究中的那些有趣话题。
可以说,这是一套充满了朝气的书,是书中的少年,有着毫不妥协的傲骨。同时这套书又是一座桥梁,沟通了学术与通识,知识与趣味,让有关中华经典的诸多问题,以清新的面目示人,通俗而不平庸,且图文并茂,便于赏读。
徐建委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