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黄土高原西方的游牧部族西羌(或简称羌、羌人),在中国历史上未若匈奴、鲜卑、突厥、蒙古那样赫赫有名。主要原因并不是他们给中原帝国带来的麻烦少—造成东汉帝国衰亡的外敌主要是西羌,而不是匈奴—而是,他们没有建立其“国家”,没有像“单于”那样势力强大的领袖,甚至缺少功绩显著可流传于史的英雄。事实上,汉晋时期华夏所称的“西羌”,是黄河上游一些统于各个部落的人群;他们只有在对汉帝国作战时,各部落才暂时结为部落联盟。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称号,但显然并不是“羌”—这只是华夏对他们的泛称。
“羌”这个字,由羊、人两部分并成。远在商代,商人便称西方有些异族为羌,大约指今日陕西东部、山西南部一带与商人为敌的人群。从“羌”这个字的构造,以及从考古资料所见商周之际北方养羊的风气愈来愈盛,且这样的混合经济人群也往南方进逼的情况看来,商人称一些西方部族为“羌”,其意是指他们心目中西方那些“养很多羊的异族”。汉代许慎在所著《说文解字》中,释羌字为“西方牧羊人也”;这应很接近商人心目中羌的概念。只是,
东汉时人所称的“羌”并非在陕西或山西,而是在更西方的青海东部与甘肃西南部。这是因为,西周以后华夏认同形成,并西向扩张;当西方的周人、秦人及西戎等都逐渐变成华夏之后,“羌”这个华夏心目中的我族边缘概念,便持续往西移指更西方的异族。秦汉时,随着帝国的西向扩张,华夏接触并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异族;他们先以“羌”这个古老异族称号来指称陇西一带的异族,后来这些异族也成为华夏后,华夏又称新开发的河西四郡上的一些异族为“羌”,最后,约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羌”才主要被华夏用来指称青海、甘肃之河湟(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一带的异族。(参见图七)在这一章中,我探讨的对象便是汉代居住在河湟地区的羌人。
由于他们与汉帝国有激烈、血腥的冲突,因此汉代之人对他们有许多的描述与记载,也使得本地各部落人群成为华夏心目中“羌人”的主体、核心。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地区指的是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一带,约在今甘肃西南与青海省的东部。地理上,本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一个个高山围绕的高原河谷是这儿最显著、普遍的地貌。(参见彩图十五至二十)河谷地区海拔高度平均约在2200米左右,高地超过4200米;一般平均海拔高度为2700—3300米。气候大致来说是冷而干燥;最暖月均温是11—13 摄氏度,有些低地可达17—21 摄氏度,年降雨量约300—400毫米。
以日月山与拉脊山为界,本区还可分为三个副区。拉脊山以北、日月山以东的湟水流域是有名的西宁河谷。湟水及其支流切割本区成为高山河谷,比较而言,本地区河谷低平,气候条件较好。河谷冲积平原与有黄土覆盖的低山丘陵,比本地其他地区来得广阔。当代这是河湟的主要农业区;在汉代,它是汉帝国军民的主要屯垦区。这儿也是黄土高原最西方的延伸部分。20世纪前半叶曾在此长期居住的英国人埃克瓦尔,曾在其著作中提及黄土与本区农业的关系。他描述道:“只要有这种肥沃而又用之不尽的土壤,加上足够的湿度或赖灌溉,简单的轮种及汉式施肥就能够保证年年有好的收成,无须休耕。”
拉脊山以南是黄河上游谷地。黄土在此呈零散分布,目前主要农业区沿黄河由东而西,有循化、尖扎、贵德等河谷盆地;这些都是河谷冲积平原及黄土丘陵盆地。汉代羌人各大部落争夺的一个主要河谷—大小榆谷—据信就在贵德与尖扎之间。日月山以西到青海湖一带则是另一区域;此处海拔较高,青海湖标高3200米。当前这里主要是牧区,较低处是良好的冬春牧场,高处是夏季牧场。汉代的西海郡就在青海湖附近。
比起蒙古草原,河湟地区的自然环境更具多元性,而高度是一决定性因素。高度影响植物的生长,因此也影响人类的农业活动。在北纬38度左右,农业分布的上限约在2700米左右。往南,到了北纬32 度的地方,农业分布上限可及3600米。森林灌木大约分布在海拔2000—3300米。在森林灌木及农业分布的上端尽头,也就是高地草原开始分布的地方。此种高地草场藏语称aBrog ;在北纬38度左右(约当青海的大通、门源一带),草场高度约在2700—3700米之间;在北纬32度左右(青海南部的班玛,四川北部的色达、壤塘一带),则草场分布在海拔3600—4600米之间。埃克瓦尔称,这是一个广大而又有多样性植物的草场,无论是食草的或是偏好荆棘枝叶的家畜,在此都能各取所需。在高地草原的最上端,植被只有藓苔类;此种植物只有牦牛能以舌头将它们舔舐下来为食。
许多到过此地的早期旅行探险家及研究者,都提及这儿由于海拔高度所造成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二元区分现象。河谷与高地不但在自然环境上有截然差异,两地居民在经济生态与社会上也大有差别。住在河谷的人被称作Yul ba或Rong pa,意思是住在低地的人或低地农人。根据20世纪前半叶的调查资料,典型的Rong pa村落大约有十几户到七八十户人家;牧地与森林公有,但房屋与田地为家庭私有。主要作物是玉米、大麦、马铃薯,西部及海拔较高处种植青稞、春小麦、碗豆等。他们通常也养一些家畜,譬如耕地用的黄牛、牦牛、骡及犏牛(黄牛与牦牛的混种),当作坐骑或载物的马与驴,以及提供生活所需羊毛与乳制品的一小群羊。
高山草原地区的游牧藏人自称aBrog pa,意思是住在高山草原的人。他们不从事任何种植,主要生活所需都出自牲畜,并以牲畜以及畜产品与农村居民行买卖交换,以取得农产品及生活所需的金属器具。游牧藏人所牧养的牲畜主要是绵羊、牦牛、马与犏牛;他们的马、绵羊与低谷农村居民所畜养的也有不同。牦牛是河湟高地牧业中最重要的牲畜。它特殊的体质,能够让它生存于高寒且氧气稀薄的环境;在其他草食动物找不到牧草的高寒地带,它仍能赖冻原的苔类植物为生;在大雪封了山道时,成群的牦牛作为前驱,可以如除雪机般为其他牲畜及牧民开路。然而据报道,牦牛们不会头尾相衔地走在谷地的小径上;即使在载负重货时,它们仍喜欢挤在一起,因此易摔落悬崖。因此牦牛强大的负载力,只适用在路较宽阔的高原地区。
借助于牦牛,20世纪上半叶河湟游牧人群的季节移动约略如下:12月到来年3月,牧民们住在冬草场,通常是在一个邻近农业聚落的避风谷地。这是牧民定居的季节。每一个家庭或牧团都有固定的冬场,每年冬天回到这里。有些冬场甚至有石房子,但大多数只有挡风的石墙或土墙,冬季帐落就搭在中间。由冬草场迁出,通常是在4月中至5月底之间,依春草发的情况而定。这也是畜类最羸弱的时候,春旱及春雪都可能造成畜群大量死亡。游牧迁移的主要形态是,先向高处移动;开始几个月移动距离短,每次停留时间也短。随着进入盛夏,畜群移动距离及停留时段都渐长。大约在八月达到最高处的草场,然后开始往下移动。早秋时已降至离冬场不远的地方,此时约是9月或10月初,这也是他们与定居藏民来往密切的季节。在河湟地区,从夏季中期至冬季中期是马肥的季节,因此一方面适合外出劫掠,一方面也需要防范遭他人劫掠。劫掠主要是为获取牲畜,对象是其他部落的牧民及往来商旅,掠夺定居村民的情形很少。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西汉中期以后,汉帝国的势力逐渐进入河湟地区。东汉时由于汉帝国驻军、殖民于河湟,造成本地羌人各部落与汉帝国间剧烈的军事冲突。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帝国史官有了河湟驻军、官员所提供的关于羌人的资料,也有了描述这些西方异族的动机。这些由东汉后期以来累积的资料,后来都被公元5世纪时的范晔写入其《后汉书》中。
根据《后汉书?西羌传》(以下简称《西羌传》)的记载,我们可以概要地重建汉代河湟西羌的游牧生活。首先,《西羌传》对河湟部落之民的经济生活有一提纲挈领的综述: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
此记载说明,基本上他们是行游牧的,但“地少五谷”这样的陈述,似乎是说他们并非绝无农业。的确,《西羌传》及《后汉书》其他篇章中都有河湟羌人从事农作或储存谷类的记载,因此学者们多认为汉代河湟羌人是兼营农业的游牧人群。亦有学者推测他们中有些是定居农民,有些则是行游牧的牧民—与当代本地藏族有农人、有牧民是一样的。以下,我由畜产构成、游牧季节迁徙、辅助性生计活动等方面,来介绍汉代河湟羌族的经济生活。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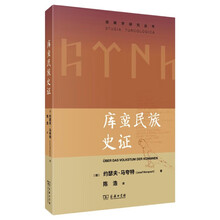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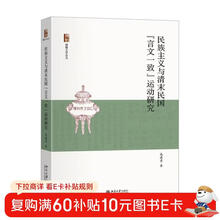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道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许倬云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铭铭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罗丰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荣新江
尽管历史事件,或者所谓“史实”并非不重要,但这本书中的“反思性研究”,却无意针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其因果关系的安排”本身,而是要将一系列相关历史事件之由以展开的根源,追溯到中原王朝的资源边界与游牧各人群的不同人类经济生态,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诸方面。正由于这样高远的立意,本书才会写得新见迭出,引人入胜。
——姚大力
王先生绝非传统的书斋型学者,他的理论背后有着大量的田野调查作为支撑。
——澎湃
他(王明珂)从“华夏边缘”出发,在田野和文献之间切换,横跨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透过常人习焉不察的现象揭示人类社会的本相,对大陆学术界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
——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