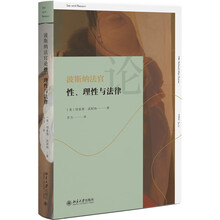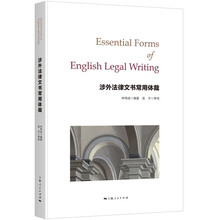《一位律师对经院教授们的挑战》:
那位博友和其他一些博友对我的回答表示吃惊,认为我本是“挺杨派”中的比较理智和清醒的人,今日说这话真是无语了。他们谴责我简直不是一个法律人。我再回应道:
“法治天下,思想中国”。我是从“思想”的角度说事的,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说事的。不少法律人往往有种倾向,认识问题相对机械和直接,缺乏思想的延伸。从法律的角度,这样说(六警是强者的代表,却被弱者歼命,故是喜剧)可能不妥;从思想的角度这样说,大致不差,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说,恐怕更是这样。
我又说: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思想探讨,不是法庭辩论。法庭辩论,我这样说,应当把我轰出去。但在思想论坛上,有人如你一般狭隘地认识问题,是不是也不受欢迎呢?
当时我们双方所争论的问题,的确涉及法律人的思维特点问题,并涉及对社会事件的法律性解释、思想性解释,以至于审美认识层次的解释问题。
我们说,盗者、抢者、杀人者应当服刑或枪毙,这是法律层次的认识(将责任归之于罪犯);
我们说,一切犯罪行为都是社会疾病的表现,这是思想层次的认识(将责任归之于社会的病灶);
我们说,武松杀人却不用偿命,挺令人愉快的——这是审美层次上的认识(只讲感情,不讲责任)。
如果能够接受以上这三种说法,我想,我当时对那些博友的回答基本没错。杨佳弑警,却被不适当地称为英雄,这的确应从社会疾病的角度看问题:它反映的是警民关系问题、政群关系问题、社会和谐的程度问题。
再用美学观点认识一下: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苏格拉底、袁崇焕事件中,都是恶的力量将崇高、正义等人类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观者感到悲伤。人们对喜剧的定义是:喜剧是对一个可笑的、有缺点的、有相当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以引起快感与笑来宣泄这些情感”。这个定义指出“笑”是喜剧的基本特征,这一认识被广泛认可。六警被杀,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相反把同情寄予本来错误的杨佳一方。从美学层次上分析,结论是极其可怕的。“‘笑’是喜剧的基本特征”,群众在“笑”什么?“笑”所表达的是他们内心的愉悦——他们愉悦什么呢?六警被杀却又被“笑”的内在“缺点”和“可笑之处”又是什么呢?除蚂蚁扳倒了大象这一点比较符合喜剧的常识之外,这个喜剧更庞大的基本构成究竟是什么呢?真的值得深思!
六警被杀却又被“笑”,其内在“缺点”和“可笑之处”不在他们个人。联系到六位警察冒着生命危险常年累月的艰苦付出,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庭是绝对应当报以深切同情的。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被“笑”,却又掩藏着一个深长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我才同意那些博友们关于六警与苏格拉底、袁崇焕一样,同是一出悲剧的观点。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但问题偏偏是,如此深长的悲剧意义,却被舆论大哗式的在群众中引发的喜剧式效果所掩——对更加本质的问题的探讨,决不是在法庭上所可以完成的。我的关于喜剧的观点,只不过一个小小提醒罢了,博友何必大大地惊诧!
法律人,是社会工作者;要真正履行好社会工作的职责,他同时还应是一个思想者;如果要做内涵丰富的思想者,那还得掌握一点美学知识。就我所知,欧美甚至台湾的许多法律人做到或接近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大陆众多的法律人,在思想论坛上听了有关悲喜剧的议论,却如在法庭辩论中听到了恶性杀人却不该偿命的话,惊诧万分,这表现了思想的差距。我们应当急起直追!
再评刀郎
刀郎音乐产生于中国西部,并曾经一度风靡大陆中国,直至现在仍在中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刀郎歌声对大陆中国人生命的打动是其他音乐——来自港台的、西方的、苍凉非洲、贫困印度乃至其他一切地域的——所无可比拟、无可替代、无法逾越的。
历史的中国的歌声,也不具这种作用。过时的中国苦难天空下所曾经颤动过、飘翔过的歌声无法在现实的中国人心中激发出如此谐洽的和声,产生如此的共鸣和震动。
刀郎音乐的本质是什么?是灾难激励下的精神昂扬,是苦难漫过大地、大地开放的灿烂之花,苦涩而优美,清澈而醇厚,激越却无半点浮飘,雷电斫劈的峭壁与浪涛的合唱,狂飙摧折的古树与风雨的共鸣,幸福天霄与苦难大地同张共震的天籁之音——是上苍对伤痛中国人心的甜美、苍凉却又无限力量的馈赠!
香港音乐、台湾音乐,在刀郎音乐面前成了富门公子哥儿们,弹指走过长街,美女背后追风,霓虹侧畔唱晚,虽力尽夸事张扬,唯雄风沉落、阳健稍逊了!
大陆高台上的庙堂之音,那些在“山蓝蓝、水清清”中颂赞高堂闲居式幸福生活的,弹拨着袒卧东床般柔情蜜意的,夸耀着历史中的炎焰张天的,在刀郎的歌声面前,或成为庸庸小者,或成为无知莽夫,一概大失颜色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