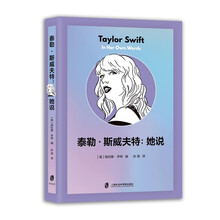对作家这一职业而言,行动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来说,这种自由却是难以想象的。所有初出茅庐的文人都选择在巴黎生活(正如桑多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需要无时无刻地跑来跑去,时常光顾咖啡馆和剧院,出入书店、报纸杂志的编辑室、出版商的客厅,以及戏剧导演的办公室。如果一个女人单独出行并在公共场所亮相,这种情形会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各种限制无处不在,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各有各的位置,并被要求严格遵循这种界限。因此,如果女人要抛头露面,就必须穿戴与她们的活动和身份相符的服饰。女客栈主、仆人、缝纫女工或是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都必须穿相应行业的服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与妓女区分开来。若是她不属于劳动人民阶层,她外出时就要有仆人相伴,这不仅仅与她个人的名声相关,也关系到她父亲、兄弟和丈夫的声誉。奥罗尔·迪德旺在饱受沙托鲁小市民们的斥责目光和流言蜚语之后,决定身着男装出入各种场合,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她小心翼翼地东奔西走,没有引起他人的非议。她成了剧院和音乐厅的常客,却没有惹起任何人的注意。那些身穿礼服和长裤的先生们行动是多么自由啊!
我看到贝里年轻的朋友,童年的玩伴们,在巴黎和我一样生活拮据,但是他们却知道所有令聪明的年轻人感兴趣的事物:文学活动、政治事件、戏剧、博物馆、俱乐部、大街小巷。他们四处奔走,见多识广。[……]而我在巴黎的街道上就如同冰上的船只。我那精致的鞋子两天就穿破了,[……]我不会提着裙子走路,身上溅了泥浆,又疲惫又感冒。我的鞋子、衣服还有被屋檐的滴水浇湿的丝绒小帽子,它们都很快破损了。
乔治·桑穿男装的主意,也是受了她母亲的启发。因为经济实用的原因,她母亲年轻时和许多其他女人一样,时常女扮男装。
起初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后来认为这样做颇有创意。童年时我就被打扮成男孩子,后来我又穿着罩衫和腿套打猎,[……]所以再穿男装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陌生,也没觉着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当时流行的款式使男扮女装变得更加容易。男人们穿着长长的、方方正正的“地主式”礼服。这种衣服长至鞋跟,丝毫也不显腰身。在诺昂,我哥哥披上这款衣服时,曾笑着对我说:“是不是挺漂亮啊?[……]裁缝一定是照着岗楼的尺寸裁剪的。这衣服想必全军团的每个人都可以穿。”我于是用一块宽大的灰呢绒布料给自己做了一件“岗楼礼服”、一条长裤和一件马甲。再配上一顶灰色的礼帽和一条宽宽的毛料领带,我看起来简直就像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雀跃着,从巴黎的一端蹿到另一端。不管刮风下雨,我都四处奔忙,不定时地回家,逛遍了所有的剧院。[……]我衣着蹩脚,模样淳朴(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略带迟钝的表情),实在无法吸引别人的目光。
奥罗尔·迪德旺就这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步人了文坛。她之所以女扮男装,就是为了能像她的贝里朋友们一样,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她用情人名字的开头字母或是他姓氏的缩写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显而易见的是,由于性别的不同,她与桑多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半个世纪以后,著名女作家加不里埃尔一西多尼·科莱特以近乎相似的方式开始了文学生涯。她让地位显赫的丈夫亨利·戈蒂埃一维拉尔用“willy”为自己早期的作品署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