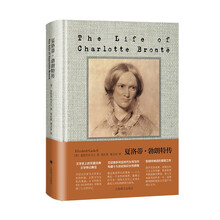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高晓声年谱》:
高晓声栖身土地庙西厢房前半间。身处逆境,他不忘默默地关爱别人。教工宿舍没厕所。韩巧娣给教工宿舍倒马桶。西厢房也有马桶。高晓声极少使用,解大手,上公共厕所,平日只用夜壶,每天清晨洗漱前自己倒夜壶,尽量不麻烦韩阿姨。那时只当永世不得翻身,心如死灰,度日如年,哪会想到若干年后冷灰里爆豆?
每天清早,睡眼惺忪,眼屎障目,拎着夜壶,出土地庙。路遇本村农民招呼:高老师……他不看人,不抬头,只是点头:噢,噢……早晨、傍晚,他踱到北塘河文昌阁一带,横着肩胛,慢慢散步。起先两年没电,点美孚灯。一个人待在阴森森的土地庙里,伴着如豆油灯。青灯黄卷,高晓声也快成泥菩萨了。
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百废待举。亿万人还没吃上饱饭。人们等来的,却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外抗帝修反,内斗地富反坏右,中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至于像高晓声之类的知识分子,伟大人物玩了一出帽子戏法:把右派分子的帽子托在手上,表现得好,摘帽;表现不好,随时随地重新戴上。摘了帽子就不是右派了?不,叫作摘帽右派,“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谁敢与阶级敌人为伍?谁敢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交友?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带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紧箍咒,正在接受一轮又一轮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政治病、身体病,在人际关系中竖起铁墙。
只有周末,高晓声与汤荣成、姚盛林相聚土地庙,抿抿小酒,土地庙才增添一丝活气。小声说话,小声匿笑。心有余悸啊。
1962年底,学校团委书记赵德荣老师和奚立华结婚,住进土地庙东厢房,隔着明堂,和高晓声做了邻居。高晓声担心自己的两种病传染给他们,不主动来往。寂寞,孤独。一夜叉一夜。
但他聪明的脑筋装着永动机。大饥荒还没过去,备课到深夜,饿了,喝点水,肚子咕咕叫。没饼干,没炉子。他打上了饭盒的主意。买点面粉,加水打糊。把饭盒盖翻过来,倒进面糊,放在美孚灯上摊饼。手捏盖边,转圈。好香!面糊加点盐,味道更好!
有天,赵德荣见他的饭盒黑黑的,问他干什么。他说摊饼的。高晓声发明了饭盒盖在美孚灯上摊饼!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住校教师竞相学样。汤荣成进而用硬板纸、锡纸罩住灯口,防止潽水。
肚子是填了,寂寞依旧难耐。
过了一阵,同事之间渐渐熟了。一天,有位老师带着笑问高晓声:“高老师,昨晚有人往你那儿送东西,你收到没有?”送东西?高晓声老实巴交说没收到,还问:“是什么东西,谁送来的?”那位老师噗嗤一笑:“昨夜有人来送饭,你怎么没收到呢?”
“送饭”!高晓声一震,马上明白,他住的房子从前一定是土地庙。谁家有人死了,第一件事就是往土地庙“送饭”,这是高晓声从小就熟悉的风俗。照老辈的说法,人死变鬼,去的第一个站头便是土地庙。土地庙几乎村村巷巷都有,它是阴间的基层组织,就像阳间的居民或村民委员会一样,离死者的家总是很近的。这么近为什么非得急急忙忙去送饭而不能回家吃?内里的含义非常复杂。细想甚至可怕。高晓声不愿意去想。1949年,新政权成立,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早已打烂,但老百姓心里并不认账。同事玩笑的意思很明白,封他做了土地菩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