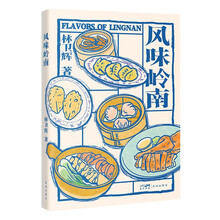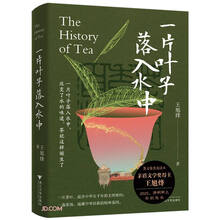《怀旧食堂:那些或温暖或微凉的美食记忆》:
小馄饨的事
馄饨一定要是薄而小才好吃,所以我一直吃不惯江南的大馄饨,无锡的、上海的馄饨都失败在大,他们的饺子小,可馄饨却大得有些不近情理,江南的林园都以小著称,为什么偏偏在吃上面那么浮夸?第一次在无锡吃大馄饨是在一座桥旁边的馄饨店,名字现在记不起来了,只知道店的牌匾是红黄两色,逛马路逛到半下午,我走得正累,又饿,刚好坐进去一边吃一边歇歇脚。哪知道馄饨端上来,多少令人傻眼,一个一个,跟小包裹似的,皮厚,是肉馅,但又有点虾米,馄饨汤里零零散散有些紫菜和海米,据说是无锡特产。
充饥倒是一流,可惜没见出好来。
后来去上海,那里流行菜肉大馄饨,也是大,菜肉饱满,我想也许是为了取悦顾客,客人来是填饱肚子的,总不能不给他们足够的量。但每次吃到大馄饨我总觉得尴尬,何苦来,有饺子有包子,何必这么大?海量奉送也不是一贯精明的上海人的风格,百思不得其解。
馄饨发源于北方,却在南方发扬光大,各地的人都根据地方的特点改进馄饨,使得这种小吃更加本土化,其叫法自然也就随之改变,比如广东叫云吞,味道保守,清淡得多;四川、重庆改称抄手,辣料自然是少不了;新疆叫曲曲,用羊肉做馅;江西人是喝汤的高手,馄饨改叫清汤。饺子、包子多少年没变过,馄饨则被改得面目全非。
有个传说也说明了馄饨的随意性,战国时期吴王打败越王,抢到了西施,可他吃什么都觉得没味。西施为了表现,跑去厨房,和面擀皮,打算做出点新式点心,哪知道做得四不像,随便包包,倒像簸箕,往水里一下,熟了就端上去。结果吴王竟然很爱吃,他问西施这点心叫什么,西施觉得好笑,心想真是无道昏君,混沌不开,就口便说,叫馄饨,加了两个食字旁,造出了—种新食品。
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越随意的馄饨越好吃,像老家那种鸡汤馄饨,真的是小而薄,都是小摊子,摆在路边。
卖馄饨的多半一对夫妻,男的掌锅,擀皮,女的包馄饨。其手法之快叫人惊叹,他们压馅是用筷子头,就点那么一点,面皮平摊在左手,用手挑肉,就那么一触肉馅,胳膊一收,朝面皮上一点,左手一握,就是一颗馄饨,老板娘再朝收纳框里一撂,就算做成了。
我看着他们做馄饨,总觉得这些人都是奸商,怎么就给那么一点肉,苍蝇腿似的,面皮也薄,再薄点就跟吸油面纸差不多——下到水里,那面皮大抵半透明。
一碗馄饨半碗皮。
走南闯北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碗馄饨,干的湿的,大的小的,我还是觉得淮南的馄饨最得精髓。超薄的面皮,一点点肉馅,清而鲜的汤头,三样的组合,再加上卖馄饨人那种利落的身手,真有点道家无为而治的意思。
刚巧也有种说法讲馄饨和道教有关。冬至之日,京师各大道观有盛大法会,庆贺元始天尊诞辰。道教认为,元始天尊象征混沌未分、道气未显的第一大世纪,故民间有吃馄饨的习俗。《燕京岁时记》记载:“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现在当然是一年四季都能吃了。
我们那里老年人尤其喜欢吃馄饨,我记得那几年我上学,住在老太家,有那么几个月,几乎每天早晨我都会端着搪瓷带花的深肚大缸子,穿越一条菜市,去早点铺端馄饨回来,那是祖孙俩的早餐。
我们那的馄饨软,入口即化,顺溜着吸吸就能下肚,老太九十多岁,吃着竟完全没障碍。我爱馄饨胜过饺子、包子、馒头乃至于一切面食,时间久了,也忍不住爱屋及乌。
直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通往馄饨铺的那条路,夏天,满街的法国梧桐,路上没什么车,寂寂的,我端着一缸烫烫的馄饨,双脚生风,又稳又快地朝家走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