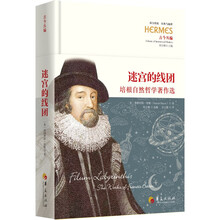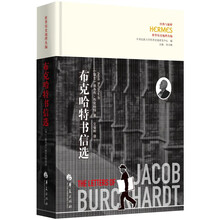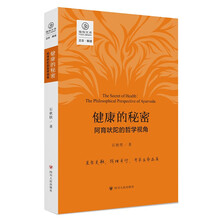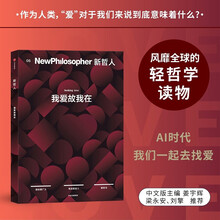面对千年来硝烟弥漫的思想战火,面对千年矗立的理性与信仰的丰碑,面对灵魂对肉体的侵蚀和肆虐,施蒂纳要用“唯一者”推倒理性与信仰的丰碑,要用“唯一者”拯救被冷落的肉体之类和被遗忘的“生命个性”,要用“唯一者”解决一切问题。也许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探索的方法确实有很多问题,但现在姑且不管这种探索的方法是否行之有效,不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行得通,它都体现着当时那个思想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思想。而那个思想的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思想的真实状况就是“上帝已死”,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了。
自柏拉图开始,传统形而上学就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感性世界,一个是超感性世界,超感性世界就是彼岸世界。感性世界只是非现实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易变的肉体世界,而彼岸世界才是真实的、现实的、理性的世界,才是永恒的、不变的、本质的世界。而彼岸世界则永远高于感性世界,超越感性世界,也规定着感性世界,形而上学就属于彼岸世界。从此,传统形而上学踏上了高歌灵魂、宣扬理性,贬斥肉体、压抑感性的征程。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当中,他把理念当作真实的存在,当作世界的本质,理念是一般的东西,是共相,是具体事物的本质,具体事物是多,理念是多中之一,是具体事物之中的统一本质,理念是事物的模型、原本,而那些纷繁多样的肉体、可感之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摹本罢了。可感之物对应感性世界,理念对应理念世界,而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它只能产生感觉,感觉是不真实的,而理念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理念世界永远高于感性世界、超越感性世界。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和理念远远高于肉体和感性。而这种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感性的失衡仅仅是这苦难的长征路上的开端而已。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盛行,柏拉图思想被宗教化,肉与灵、感性与理性不但没有趋于和谐,反而是走向了更加极端化的失衡。在基督教的世界里,灵魂之类被奉为神明,最终以上帝的身份加以膜拜,而可感之物、肉体之流则被踩在脚下,当作罪与恶的象征,仅仅充当了撒旦的工具。肉体之类被当作灵魂步人天国的绊脚石,天国是每个灵魂的诉求和最终归宿。柏拉图的思想基督教化后,直接的后果就是肉体和感性被贬得一无是处,地位卑微,而灵魂的地位则至高无上。
在基督教思想束缚这个世界几百年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用了一句经典的“我思故我在”敲响了基督教的丧钟,这一宣言看似简单易懂,而背后潜藏的是:只有经过思维的检查和明证,可感之物的存在才确实存在、真实可信。这无疑使肉体和感性之类的独立存在画上了问号。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基督教的思想里,肉体之类已经人人唾之、任人践踏,而到了笛卡尔这里,肉体之类的存在又备受质疑。在这之后,肉体之类在理性、观念的践踏下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到了黑格尔那里则达到了极致。
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体系当中,肉体只是源于灵魂即绝对精神,只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种结果和产物而已。绝对精神作为太阳神,普照大地,包括肉体在内的一切都是太阳神的子民,其他一切都生于绝对精神、源于绝对精神、低于绝对精神。肉体之类地位卑微,声名狼藉。黑格尔又利用辩证法,说肉体始终是在默默地背离着灵魂,而不是完全彻底地依附于灵魂,肉体被当作一种佯谬消解掉。黑格尔看似是把这亘古以来遗留的失衡与不和谐的问题彻底地解决了,其实不然,黑格尔只是在柏拉图、笛卡尔等人的身上加上些粉饰,迷惑众人罢了。
肉体与灵魂的失衡与不和谐绝对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消失,也绝对不是简单地在前人的身上加些粉饰就能迷惑他人,更不是在绝对理念的光照和普度下就能真正解决的。肉体、可感之物不能皈依于灵魂、理性,更不能消失,肉体、可感之物有他们自己的特性。如果我们非要为灵魂的高尚尊贵而执意摆脱肉体之类的负重,那么我们就会变成灵魂的附庸,变成理性的幽魂,变成无肉体的虚空,而灵魂的附庸、理性的幽魂正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结果。在这探求的道路上,生命的力量、感性的涌动则逐渐暗淡、逐渐褪色。
施蒂纳正是看到了几千年来肉体之类的窘境,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理性、观念、精神的过分溺爱。施蒂纳厌倦了这种肉体与灵魂的失衡、厌倦了无孔不入的精神至上、厌倦了肆无忌惮地对理性的追捧,厌倦了神魂颠倒地对上帝的崇拜。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