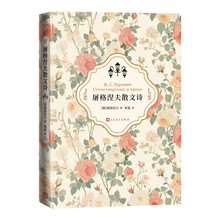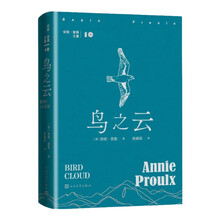标志的运用,在诗人手里和在艺术家手里不同 我还注意到斯彭斯的一个奇怪的论调,很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诗与画的界限考虑得很少。他说:"说来很奇怪,诗人们一般对文艺女神们的描绘是极稀少的,稀少的程度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诗人们和文艺女神本来有特别深的关系。" 这不就是认为诗人们说到文艺女神时不用画家所用的那种无声的语言,是一件奇怪的事吗?乌拉尼亚对于诗人们是天文学的女神,从她的名字和她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可以认识她的职责。艺术家为着把她的职责很清楚地表现出来,就得使她用一根棍子指着天文仪;这根棍子、这个天文仪和她的这种姿势就是艺术家的字母,用来拼出乌拉尼亚的名字。但是诗人想要说"乌拉尼亚老早就已根据星宿预言到他的死"这么一句话时,他为什么一定要向画家表示尊敬,添上一句"乌拉尼亚,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面对着天文仪"呢?这岂不是就像一个人本来能够而且应该把话说得响响亮亮的,却还要运用土耳其后宫里哑巴太监们因为不能说话而造出来的那种符号吗? 斯彭斯还在另一个问题上发表过一个奇怪的论调,那就是关于道德方面的神,即古代人认为掌管道德品质和人类生活行为的那些神。他说:"值得指出的是罗马诗人关于最好的道德方面的神所说的话少得出人意料。艺术家们在这方面却远较丰富,谁要想知道这类神中每一位的容貌衣着,只要去请教一下罗马皇帝们的钱币就行了。诗人们固然也时常把这类神作为人物来提,但是一般很少谈到他们的标志、服装以及外表方面的其他事项。" 诗人就抽象概念加以人格化时,通过他们的名字和所作所为,就足以显出他们的特征。艺术家却没有这种手段可利用,所以就得替人格化的抽象概念找出一些象征符号,使它们成为可以辨认的。这些象征符号并不是所象征的东西,意义也不同,所以就变成一些寓意的形象。 在艺术里,一个女人手持一条缰绳,另一个女人靠着一根柱子,她们都是寓意性的人物。但是在诗人手里,"节制者"和"坚定者"并不是寓意性的人物而只是人格化的抽象概念。在艺术家手里,这些寓意人物的象征符号是根据需要来发明的。除此以外,他就没有其他办法使人了解这一个或那一个形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至于诗人,他为什么要把艺术家迫于需要所采取的办法强加给自己呢? 斯彭斯所认为奇怪的事,对于诗人们来说,却值得规定成为一条规律。诗人们不应该把绘画的贫乏看成它的财富。他们不应该把艺术为着要赶上诗而发明的手段看作一种值得羡慕的完善(或优点)。艺术家在用象征符号来装饰一个形体时,他就是把它从一个单纯的形体提高到一种较高尚的人物。但是诗人在利用这种画艺中的装饰时,他就是把一个较高尚的人物变成一个傀儡。 这条规律通过古代诗人的遵循而得到证实,而对这条规律的蓄意破坏则是近代诗人最欢喜犯的错误。近代诗人的想象人物都戴着假面具行走,凡是对这种假面具把戏懂得最多的人,对作品中主要的东西也就懂得最少。所谓主要的东西是指让人物行动起来,通过行动来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不过在艺术家们用来显示抽象概念的那些象征符号之中,倒也有一种是可以而且也值得用在诗里的。我指的是不应看作寓意而应看作工具的那一种符号,这些工具由诗人联系到某种人物时,是那些人物在实际生活中所必须用的。"节制者"手里的缰绳和"坚定者"所倚的柱子都只是寓意性的,所以对诗人就没有用处。"公正者"手里的天秤就不只是寓意性的,因为天秤的正确运用其实就是公正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文艺女神手里的竖琴或笛,战神手里的矛以及火神手里的铁锤和火钳就完全不是象征符号而是单纯的工具,没有这些工具,这些人物就不能做出我们认为他们做过的那些事业。古代诗人有时放进他的诗句中去的那些标志,都属于这一种;因此,我想把这一种标志称为"诗的标志",以别于另一种,即寓意性的标志。诗的标志代表事物本身,而寓意性的标志则只代表某种类似这事物的事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