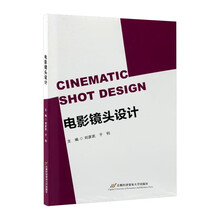《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
传统文化的认同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容置疑的,很少有人不需要它。如果传统文化的认同人群能突破种族的界线限,扩充到其他强势文化的种群中去,岂不更证明这传统文化魅力的强大。这样的想象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里是最自然的,它深刻说明传统文化的认同基础不可能囿于国内现实,它逃不脱全球化的背景。与其在制作影片时想象并期待传统文化获得强势文化人群的认同,不如直接在影片中设置一个西方人。他介入,他见证,而且他受感召。以一个西方他者的认同,来确证并加强自我的文化的独特价值,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诸多电影都陷入了这种种族的文化想象中。这批影片包括《红河谷》《红色恋人》《黄河绝恋》《西洋镜》《紫日》《刮痧》《庭院里的女人》……
从《洗澡》到《刮痧》,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电影中相通的文化表述。比较而言,《洗澡》的表述更执着、从容,而《刮痧》创作者虽对“文化冲突”命题跃跃欲试,但到了“美国”这样一个具体的创作环境中,创作心态失去了平衡。影片前半部分是一种带着攻击性的“文化冲突”的极端情境,但这个主题在影片后半部分逐渐衰微,矛盾的化解方式是向一个为维护亲情的历险故事转移。就主题的表达而言,显得虎头蛇尾。不如《洗澡》中可以将文化命题在纯粹的想象世界里从容布局。《刮痧》一时遭遇非常具体的文化现实,逃避和转移是唯一的出路。
《刮痧》中的“文化冲突”如何化解,影片主人公许大同的命运如何转折,是影片叙事的关键。这个转折的动因正是许大同罪名得以确立的动因——美国公司老板。也许是对许大同获罪之后惨状的同情和内疚,也许是对“刮痧”的好奇、疑惑,甚至是他不甘心失去一个好员工,他最终来到了唐人街。在一个布满瓷器古玩的密室里接受了一次刮痧治疗。这一场景在象征的意义上应该是一次“文化交流”。刮痧医师并未跟这位西方人讲述刮痧医疗原理——由于中医与西医分属完全不同的医学系统,刮痧原理在这种场合是不可解释的,正如许大同在听证会上努力描述的“七经八脉”会被认为是一派胡言一样。但刮痧师深谙两种文化间的种种世故,他巧妙地将刮痧与西方人已经接受并熟悉的东方符号按摩与针灸作了一次通俗的类比。这种“交流”实际上意味着一个“异文化”要获得西方人的认同,需要借助的是西方人自己的文化语汇。也就是说,这公司老板如果不调动他自己文化系统中的“存货”,刮痧仍是难以索解的。但公司老板最终看到了镜中自己的后背:缕缕鲜红的刮痕,他终于恍然:如果没有用自己的身体经验,西方人在东方这面镜子中看到的将仅仅是“伤痕”。这一矛盾一旦解开,许大同案情实际上已经解开,而此后的一切矛盾、追逐、铤而走险,完全与“文化冲突”无关了,最后只是“交流”被“科层体制”延宕而已。而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影片却不失时机地对美国人基于自身的伦理价值观所表现出的敬业精神进行了极大的褒扬,前半部分在法庭上表现出的对异文化的傲慢与轻视被轻巧地消解。最令人尴尬的是,无论是许大同,还是其妻简宁,面对一个文化歧视和文化误解的现实,表现得毫无智慧。影片一开始似乎郑重其事地要讲一讲“文化冲突”,但它虚晃一枪,只讲了一个英勇的父亲,他为了重新获得被法律隔离的孩子,放弃一切,并铤而走险。矛盾从“文化冲突”转变为普遍性的人类情感表达。当公司老板与地区法院律师赶到简宁家通知许大同无罪时,女主人公泪如泉涌,似有“受宠若惊”的成分,因为她早已丧失了为匡扶义而奋斗的勇气和意志。而许大同在窗台上悬于一线的生命是由公司老板的粗壮臂膀拉上来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