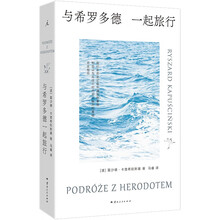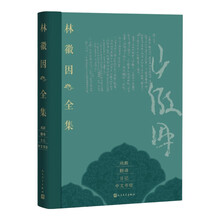上
----------------------------------------
百年传奇
----------------------------------------
一个名叫沙依诺夫的成都人
----------------------------------------
沙依诺夫回忆录
----------------------------------------
沙依诺夫回忆录中文译稿是从沙依诺夫俄文笔记本第57页开始,第1页至56页遗失,仍在寻找中……
----------------------------------------
对?峙
1914年,沙依诺夫从俄国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分配教小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征兵上前线,在战壕中与德军对峙。
1
但就在这个晚上,我的眼睛出了问题,我不明白,我的眼睛就像被蒙住一样,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后来来了一个兵把我领过去,大夫给了我一些药,用药以后这种情况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头一晚我们连的一个少尉要带我去侦察,连长没同意他这么做,连长给他解释说:“新兵初来前线,首先必须搞清自己阵地的位置和情况,只有在弄清自己阵地的情况后才去侦察。”
后来在一次休整期间,我们连的一个年轻准尉告诉我,当时那个少尉去侦察时带了一位新来的军官一起去,但返回时带着那位新来军官的尸体。少尉详细告诉了连长事发的经过,说新来的军官被德国人打死了,而少尉则瞅准机会将他背了回来。部队在此地停留了几天。那些天我到阵地最前沿只去过两三次。换防后,我们被安排到了一个村子里休整,休息两天以后,我们连队的头头们去勘察了此前废弃的战壕和掩蔽所,以及撤离时的周边地形。那些战壕里满是积水,掩蔽所也全部坍塌。
这一地带地势平坦,不过,遍布致命沼泽。进出战壕的通道因此都是很难行的。我们沿另一条路返回,路也不见得好多少。我紧随其他人之后,机警地环顾四周,一不小心我一脚踩偏,立刻掉进一段废弃的战壕里,陷入齐胸深的泥潭,这段战壕里积满了水。时值深秋,水又冰凉,大伙立刻把我拖出战壕,决定返回村里。当我们步行到宿营的村庄,天空已经是星星闪烁。勤务兵已经在街上升起篝火准备晚饭。我冷得牙齿打战,急忙换了衣服坐到篝火旁,一边取暖一边烤衣服,我想弄不好要大病一场。结果只是虚惊一场,甚至连轻微的伤风感冒都没有。过了两天,我们的少尉说他病了,紧接着就卧床不起。这时,一个上级当官的带着随从经过我们驻地,我们连长陪着他到处走走看看,不经意间走进我们住的农舍。一声口令“军官先生们到!”按照条例,除了病号以外,我们全都站了起来。和我们连长以及其他人略为摆谈几句后,当官的问道:“这个人怎么躺着不站起来?”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而在当官的进来后没有站起来立正。要知道,在当官的进来时,在床上睡觉的少尉应该清楚地听见“军官先生们到!”的口令。听到这个口令,所有人都应该立即起立立正。
我们连长告诉当官的说这位少尉病了。当官的命令立刻把少尉送到部队的野战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当官的离开以后,少尉由一个人陪同送到了部队的野战医院。过了一天,少尉的勤务兵从野战医院回来,收拾好少尉的东西,说病人马上要被送到后方医院,他也随同去了后方——他俩都是西伯利亚人。少尉走后,上面来人进行调查,但已见不到他本人,然后在士兵中就出现一些传言,好像他是持有别人的证件当上了少尉。但这件事情是否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团休整六天后,又开拔到另一个地段去换防了。我们全团以急行军速度行进,因为命令要我们尽快和尽早赶去替换先前布防在那儿的那个团。如此急迫地从前线撤换下这个团,在这个时候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团变得不可靠了。当天我们就遇见从前线撤换下来休整的一支部队,在队伍中我看见了我过去在步兵预备役105团时的连长。由于不允许停留,我们俩只来得及相互喊了一声“保重!”行军途中,我们部队只作了两次短暂的休息,时间刚够抽完一支自制的卷烟,又继续急速前行。午夜时分,我们赶到前线。
2
上头严令禁止我们与前线换防的这个步兵团的人说话。理由是要保持安静。实际上我们也无法与那个团的人说上话。因为被换下来的这个团接到命令走一条路,我们走的是另一条路,本来就相互打不了照面。最高领导当然知道,为什么急着让我们走另一条路把他们换下来,所以才严禁我们和他们交谈。进入换防地段后,我们沿战壕派出了明哨和暗哨。夜里我们要去查岗几次。按条例,暗哨是可以不查的。不过,真实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值暗哨的士兵们不顾危险,或打瞌睡,或卷烟抽。所以一定是要查岗的!被换下去的部队撤走后,对面德军中的一位德国人用纯正的俄语高喊起来:“喂,俄国佬,俄国佬们听着!”“你们这些548楚古耶夫团的士兵们到这新的阵地,你们要和平表现自己,不要开枪,我们也不会开枪,不过如果你们不听劝告,那我们就只能把你们扫平。”我们进入这片阵地还不到半小时,他们就知道我们部队的番号,这简直不可思议。他们居然如此快地就知道我们来换防。第二天早晨,我们透过战壕护墙上的观察孔发现战壕对面有一座德国佬用水泥浇注的地堡,它距离我们很近。我们排的士兵们对他们的存在视而不见,也没有谁从战壕里探出头去认真观察对方的部署。
前线变得平静。第二天晚上我们决定秘密地从所有暗哨位置铺设一根绳至掩蔽洞,而且在掩蔽洞入口前的绳上面挂上空的罐头盒,遇有情况,暗哨就会拉绳通知我们,我们就能提前预防危急情况发生。作为暗哨,众所周知是不许说话,更不许吸烟。不过一位当值暗哨的士兵不顾禁令,想抽烟了,他身上没有火柴,就擅自去另一位暗哨处要火柴。他一不小心脚碰到了消息绳,弄响了那些空罐头盒。大家伙儿听到警告立刻抓起枪冲出掩体,这次警报当然是虚惊一场。我们又听到了对方用俄语喊道:“俄国佬,听听吧!” 紧接着德国人也制造了与我们完全一样的声响。然后又问:“这样干到底好不好?” 这意味着他们一直在听着我方的响动,随时在监视着我们。在我们排的这块地段一切还算平安无事:我们没开枪,德国人也没有向我们开枪,只有唯一一次例外。
那是一天早晨,一个被提前征召来的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士兵登上深壕护墙的观察哨位站岗,我严令他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别从护墙探出身去。就在我和排长离开他去掩蔽洞轮流睡会儿时,这个年轻战士忍不住好奇心,爬上窄梯探出头往外看。他露出头用望远镜观察德军的阵地。后来从其他士兵处了解到,德军方面只开了一枪,这个士兵就从梯子上栽了下来,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妈妈”,同时还用牙齿咬着军帽。他立即被抬上担架,不过此刻他已经断气,再无需医生的救助了。本来,其实不要望远镜,也看得见对方地堡的情况,因为对方的战线离我们不足一千步,双方之间的距离肯定是被对方精确地测量过,所以他们射击非常准确。
这件事发生以后,大家都变得更加小心,再也没有谁敢把头露出战壕了。我们连右翼有一条叫“杰辛卡”的小河,对岸是另一个营的防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由上司陪同一些军官来到阵地,登上了战壕,也是用望远镜观察德军的一些火力支撑点。其中一位军官有一只猎犬,它老在铁丝网之间刨地,我们从自己的散兵坑里注意到这点,感到很惊讶:我们连的那位士兵刚伸出头就被对方放倒了,而现在这一大群人,却没有谁找他们的麻烦?这群军官看了好大一阵,然后退了下来,各自进了掩蔽所。此时德国人开始有针对地向军官们进的那些掩蔽所开炮,毫无偏差。这些阵地以前曾经被德军占领过。一阵炮轰后,我方死伤无数,不过没有一发炮弹落到我们这片阵地。
看来德国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因为我们按照他们的建议表现良好。在离我们这个排驻防大约有半俄里①的阵地坡上,一座塔台好几次被设定为观察哨。当我军炮火开始射击的时候,即当需要时,我们应该从这个观察哨向炮兵提示调整弹着点。一天傍晚,准尉沃托奇科被命令上观察哨观察敌情,他听到德军方向传来斧头劈木材的声音(当时太阳已经落山)。他马上电话召唤我们的炮兵。炮兵还没有来得及开炮,对方就安静下来了。然后我方炮兵还是发射了三四发炮弹才停止。德国人没有反应,对这个观察塔台从没射击。为什么呢?这引起了上级指挥官们的注意,因为这个观察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这个观察哨已经无数次指引过炮兵射击。为什么他们不向这个观察哨射击,不把它击毁?这座观察哨四周所有的大树全部都被损毁。所以上面派了几位志愿者去侦察,如果发现有电话线就会被切断。这个塔台观察哨前面有一个大的湖,湖那边又是德军的阵地,因此,一天深夜,完全由士兵组成的侦察兵们发现连接到这个侦察哨的一条电线,这根线被人为地做过伪装,铺设在这个湖的水下面,侦察兵们切断了这个通信联系,顺利返回。上司给他们放了一个月的假。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回家与亲人相聚的待遇,只有严重伤残住院出院后,才能享受到。我们另外一个连队战壕前方,可见杰辛卡河那边德军火力支撑点远处有德国人的一处堆积木垛。我方的炮火曾经打到这个木垛,但是它没有被摧毁,只是打歪了立在上面的一个十字架。从这个点上,德国人可以非常容易地观察我们的情况。比如,如果白天任何一个人被派往后方,那他只能够走到路边立着的一个小纪念碑,就会被击中,不是伤,就是死。
在我们和德国人的战壕之间,小河再偏右一些的地方有一座由几幢房子组成的小院落,是一个酿啤酒的作坊。晚上我方和德国人都经常去那里侦察,但双方从未发生冲突。我方离开后,德国人才去。在一次侦察行动中,我方一位侦察兵察觉原在地板上的一堆杂物似乎被挪动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挪到了另一处。
这座小院已经被当地住户遗弃,是谁挪动的杂物? 此前这位侦察兵没有发现这一点,当他注意到这点,然后就打开木地板,他撬开了一块地板后发现了一个地窖。“兄弟们,这里有一个地窖!多半下面有德国啤酒!”大家又撬开了一块地板,下到下面后,发现不少大的啤酒桶,经过一番翻动,结果非常遗憾地发现全是没装啤酒的空桶。不过在最后一只桶下面,大家发现了一个手拿电话坐在那里的人,就这样他们抓到了“舌头”。这是我方侦察兵们给我讲的故事。我其实经常偷偷跑离阵地到阵地后方去,躲在被炮弹炸出的深坑里给喀山和家里写信,不过从未收到过一封回信。一天傍晚,整个德军防线方向传来一阵类似于 “乌拉”①的高喊欢呼声,而我们没有发现他们有行动。稍后,连长的通信兵来了,告诉我们德国人拿下了里加。我们在这里一直守到秋天。我被派到137师司令部。在穆斯林士兵大会上,我被选为该师穆斯林委员会主席。我多次尝试推脱,解释说我太年轻,不懂政治,请他们另选一位年长的少尉来替换我当这个主席。不过他们告诉我这位少尉已经到军司令部克雷连科准尉那儿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