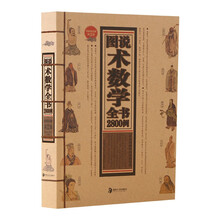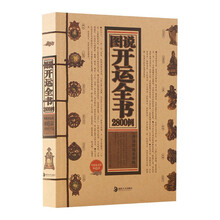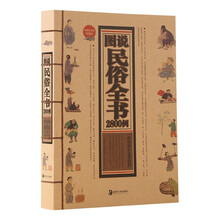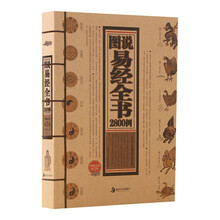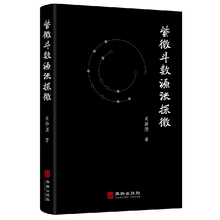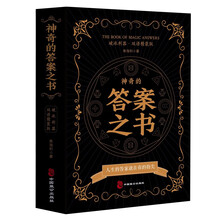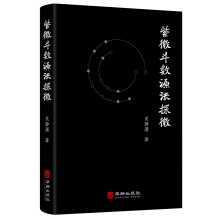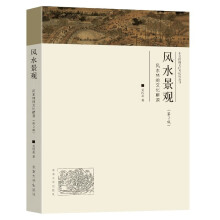《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诗经日食”
“诗经日食”和“书经日食”都是中国古今学者、西方汉学家和日本学者热衷于研讨的历史谜案。“书经日食”留待下一章讨论,这里先谈“诗经日食”。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话。由于中国古代用干支纪日,六十干支周而复始,历数千年而不乱,所以上面这短短12个字,已经交代出颇多信息:在十月份发生一次日食,这天的日干支是辛卯。于是就有学者发生寻幽探胜的兴趣,试图推算此次日食的确切年代,不料越探索“谜”却越大。
和彗星回归之类的问题不同,对于日食,中国古代很早就会推算,当然也可逆推。早在梁代(公元503—557年),天文学家虞刖就做了推算,他认为“诗经日食”发生于周幽王六年,换算到公历,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近代学者朱文鑫根据《奥泊尔子食典》推算,也得到同样结论。而近代日本学者平山清次、能田忠亮则论证“诗经日食”是发生于公元前735年(周平王三十六年)11月30日。于是形成“幽王说”与“平王说”两派,长期论战不已。近年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平王说”。
日食是一种很特殊的天象,每次日食,在地球上只有很小一部分地区可以看见;在可见区域内,不同地段中所见的食分等情况也不相同。“平王说”的主要理由正是基于这一点,这可以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教授的论述为例。他分析了周代厉、宣、幽、平、桓、庄六王在位期间共200年内的全部日食,其中发生于十月且发生之日的日干支又是辛卯的共有4次,这4次中有两次在中国全境都看不到,另两次即前述争议中的。其中幽王六年那次在今内蒙古西部、宁夏北部一带才可看到小偏食,而在周朝首都看不见。只有平王三十六年的那次唯一可以当选。
但是,“平王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此说与《十月之交》的诗意不合。我们毕竟不能将一首诗与一项天象记录等量齐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有关诗句抽出来,并将这些诗句视为一项天象实录,据此大加考证,却不考虑这些诗句在原诗中的地位与作用。《十月之交》原诗头两章如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诗人把日食和月食都看成不祥的征兆,认为这是由于政治黑暗,所以上天示警。所谓“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所谓“四国无政,不用其良”,皆为乱世光景,所以上天让“日月告凶”。这与古人“天垂象,见吉凶”的传统观念是完全一致的。《诗小序》说“《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认为此诗是大臣为讽刺周幽王而作,应该是有些道理的。此诗第三章还有“百川沸腾,山冢奉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等语,诗人所见的乱亡之兆,还不仅是日食月食,又旁及于山川,可叹当政之人,何以还不警惕省悟。周幽王正是西周的亡国之君,他死后平王东迁,建立东周,方才稍有振作,有了一些新气象。《十月之交》的诗意,与《诗小序》“大夫刺幽王”之说及幽王时的史实都很吻合,那么诗人又怎么可能在诗中咏叹起几十年后的未来天象?如果要确认诗人所咏为平王三十六年的日食,那就必定要将此诗的写作年代后移40年,而这样一来,整个诗篇的内容和情调就全与史实不合,变得难以索解了。
两说各有其道理,也各有其困难,所以争论也还会继续下去。不过,笔者个人倒有点倾向于“幽王说”。公元前776年9月6日那次日食,虽然在周朝首都看不见,但在西北边疆毕竟是看得到的,诗人所咏,会不会是得之传闻呢?我们后面就要看到,日食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视的天象,边疆所见,也大有向中央报告的可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