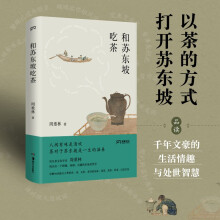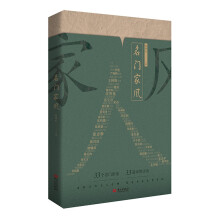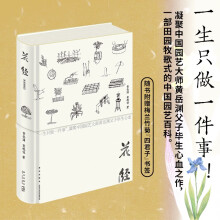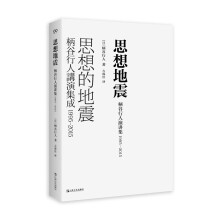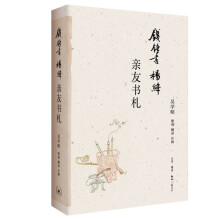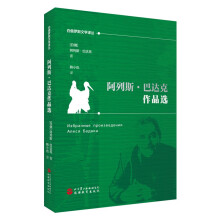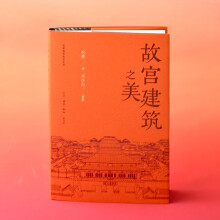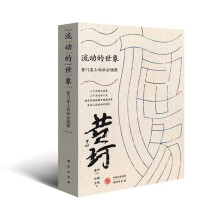《蠹鱼文丛 浙江籍》:
去岁暮春,我为《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撰写书评(载2013年3月3日《上海书评》),文末表示:“据笔者所知,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高伯雨、郑子瑜等也属于‘一心倾向周作人’者的大量信札依然存世,期待也能早日整理出版。”没想到时隔仅仅一年,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书札就惊现北京匡时2014春季拍卖会。
郑子瑜(1916-2008)是福建漳州人,为清代诗人郑开禧后裔,1939年南渡北婆罗洲。他自幼喜爱文史,21岁就主编《九流》文史月刊,后倾情于散文创作。1954年移居新加坡后曾主编《南洋学报》,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美国阿里森那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校研究或执教。他长期致力于周氏兄弟旧体诗、郁达夫旧体诗、黄遵宪与日本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尤以对古汉语修辞的研究为海内外学界所推重,所著《中国修辞学史稿》为世界第一部国别修辞学全史。
在与周作人通信之前,郑子瑜就与郁达夫、丰子恺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家有所交往,本次同时付拍的丰子恺1948年至1950年间致郑子瑜的9通书札就是一个明证。他与周作人通信始于大陆“反右”运动告一段落后的1957年8月26日,终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的1966年5月11日。这批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存有原件也即此次付拍者,总共84通,并附吴小如致郑子瑜、谢国桢致周作人和周艾文致周作人信札各1通,又周作人作《(郑子瑜选集)序》手稿等。
然而,这还不是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的全部。这就要说到我与郑子瑜的关系了。1980年代初,因研究郁达夫,我与郁达夫研究史上第一位编订《郁达夫诗词抄》的郑子瑜取得联系。以后不断向他请益,他也为《中国修辞学史稿》出版事委托我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多次交涉。而我们之间第一次成功的合作是,由郑子瑜保存的周作人《知堂杂诗抄》手稿经我略作增补后推荐给钟叔河主持的岳麓书社出版,时在1987年1月。郑子瑜在为《知堂杂诗抄》所作的《跋》中追忆了与周作人的交往始末,以及他谋求《知堂杂诗抄》出版的简要过程,笔者因此得知他珍藏着周作人的大批信札。当时因他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客座,直至他返回新加坡,才于1993年2月寄赠我周作人致其书札影印件一套。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套影印件连同邮寄大信封均保存完好。
有意思的是,郑子瑜惠寄我的周作人书札影印件与此次付拍的周作人书札颇有出入。首先,郑子瑜是细心人,已对周作人手札按写信时间先后作了编号,此次付拍的84通书札原件最后一通和我收到的影印本最后一通右上角注明的编号均为95,可知周作人寄给郑子瑜的书札前后总共95通,这个数字应是确数。其次,此次付拍的周作人书札原件为84通,我收到的影印本则有86通。经仔细核对,有原件而无影印本的书札为4通,无原件而有影印本的书札为6通,有编号而原件和影印本均无的书札则为5通,这5通恐怕真的是不明下落了。第三,影印本所有的一些附录,如周作人1961年7月18日致日本实藤惠秀函抄录稿影印件等,也为书札原件所缺。最后,书札原件除了编号,还加注写信年份;影印本除了编号和加注写信年份外,更注明每通信寄往新加坡还是东京,还注明已缺了哪些书札,如编号18的信上注明“(17缺)”等。令我特别感动的是,郑子瑜担心我无法辨认信中的某些字、词和内容,还在不少信上加注说明。
因此,我探讨这批周作人致郑子瑜书札的学术价值,以此次付拍之84通原件为主,以我收藏之郑子瑜惠寄影印件为辅,以求更为客观和全面。这84通书札原件均为毛笔书写,或端正或随意,可充分领略周作人独具一格的书艺自不在话下。而信中与郑子瑜互通音问、切磋学术、赠送资料和闲话家常,又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周作人1957至1966年间的生活、写作和心境,也毫无疑义。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信中不断与郑子瑜讨论《知堂杂诗抄》的编选,这批书札呈现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知堂杂诗抄》成书轨迹,从而大大有助于我们对《知堂杂诗抄》的研究。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