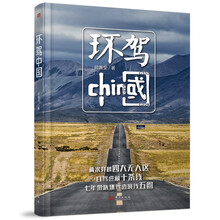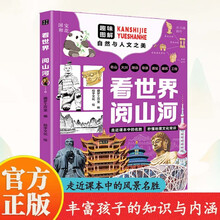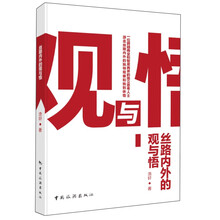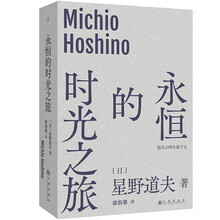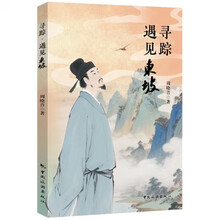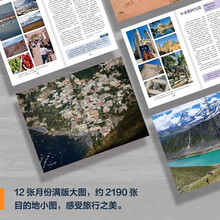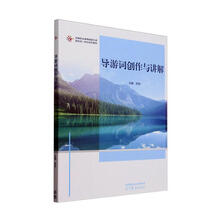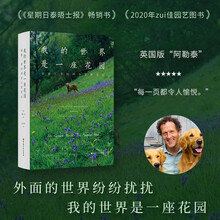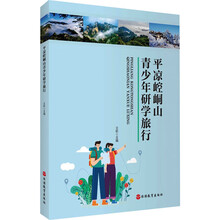《旅途花开》: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又一个正月初四日,是我回家乡串亲戚的时候了。多少年来,我都遵循着家乡的习俗——过了正月初一,出嫁闺女便可回家给父母、长辈磕头了。
每到此时,我都格外想念家乡,想念自家的人,想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们。包括门前的老槐树,地里的老牛,甚至会忽然想到村里谁家的一面迎门墙,或厚厚的两扇木门,一个个特写,一幅幅场景,就像一部纪录片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我是在他们和它们的目睹和陪伴下长大的,有时候哪怕只想起一人、一物或一个场景,就像扯住了一根穿有童话的线,随即牵出我童年时大串儿大串儿的故事,心里就融融的、暖暖的,像有一股涓涓细流在我的心田流淌,滋润而舒缓,让我对家乡充满期盼和向往。
向往着与家人和邻里们围坐在饭桌前,边吃边聊天的那份温馨和惬意——又到了这一天……
近午时,到了我家的门口。
过年时,正值村民们农闲,每逢此时,我回家乡,总有街坊邻居到我家来——平日里他们都喜欢互相串门儿,好找我弟弟聊天。
餐桌上摆的都是大碗大盘盛的各种炒菜,炒鸡蛋、煎豆腐、鸡鸭鱼肉样样有。
大家几盅酒下肚,他们中有的脸儿红了,眼角也有了些眵目糊了,说话舌头根儿有点皱,却声高话稠了:他们争相夸自己承包塑料大棚的管理技术高,说自己种植的蔬菜如何新鲜、水灵,黄瓜长势如何旺,说个个黄瓜顶花带刺儿,吃起来酥脆爽口……村支书也带头承包,亲自骑着自行车,后车架上挂着盛满黄瓜的两个大筐走街串巷地去叫卖呢。用支书自己的话说:“支书咋了?也是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你的大棚要是不好好去管理,黄瓜秧子照样废。”他是我家对门住着的李二叔,上任当了支书,还跟往常一个样,有空儿就来我家串门儿。他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是位厨师,所以他来我家串门儿时还时常展示一番他的厨艺呢。北头的一个本家弟弟说他爹大年三十起高烧不退,可老人家坚持不去看病——村里有个错误观念:过年看病吃药,这一年都会生病的。所以,说破天他也不去医院,儿子儿媳这次没听他的,没商量,去医院把医生请到家里,经过检查,老人得了肺炎。医生说要是再耽误,问题会很严重。老人不愿意去医院,就在家输了三天液——烧退了。
“现在大叔怎么样啊?”我问。
“好多了,之前整整两天不吃不喝,昨天说饿了。这会儿家里大米白面、猪肉羊肉啥都有,问他想吃啥,立马儿去做,大叔想了半天说,就想吃块煮红薯。”这句话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
我在大家的笑声中品出了欢乐和幸福,听出了熟悉和亲切,感受到了浓浓的乡音和乡情。
这时,我的侄儿又端上了一碗红烧肉,弟弟叫我母亲坐下来一块儿吃,可我那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却一直顾不得在桌旁落座——不断地被街坊邻居领着亲戚来磕头的人喊去“请头”呢。虽然我们替她累,母亲却是很高兴。她拧着小脚,迎送着来给她磕头的晚辈。直到过午时分,我娘才在早为她放置好的头把椅子上坐下来。看得出娘虽然忙碌,可是很开心,很享受。娘不停地给我夹菜,给坐在桌上的邻居让酒,还高兴地扭着脸儿对我说:“你看,如今村里的日子好过了,来磕头的大人小孩儿都是从头到脚一崭新,像你小的时候,你爹从城里开会回来给你买了个黄色的‘米腊儿’(塑料的)卡子,把邻居家的小闺女都给稀罕住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