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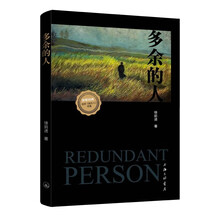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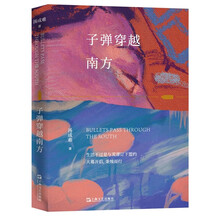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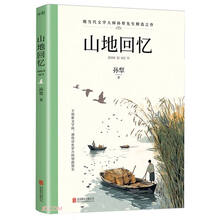




★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经典代表作
★精典名家小说文库系列小说之一。精装版本,著名画家何家英提供封面及图书插画,并特制精美藏书票,集文学与艺术于一体,兼具经典性和收藏性
★名家+名作+名画,中国人提升文学修养的必读书。
柳家大少爷娶亲,迎亲队伍在回家途中,遇到了土匪。为了保护美丽的新娘,驮夫五魁背着新娘逃跑,但最终没有逃过土匪的追击,新娘被抢走了。当夜五魁冒死深入匪寨,设计从土匪头领手中救出了新娘。两人千辛万苦回到柳家,柳家大少爷却因为猎枪走火,炸飞了双腿,成为了一个废人。新娘没有如五魁所愿,成为让人羡慕的柳家少奶奶,反而沦为了大少爷发泄的工具,五魁不忍女人所受非人的折磨和屈辱,带着女人逃进了深山老林。最终,女人因五魁杀死了与她亲昵的狗而羞愤自杀,而五魁则由一个坚持不碰女人一根手指的男人变成了一个拥有十一位压寨夫人的暴戾土匪。
迎亲的队伍一上路,狗子就咬起来,这畜类有人的激动,撵了唢呐声从苟子坪到鸡公寨四十里长行中再不散去。有着力气,又健于奔跑的后生,以狗得了戏谑的理由,总是放慢速度,直嚷道背负着的箱子、被褥、火盆架、独坐凳以及枕匣、灯檠、镜子,装了麦子的两个小瓷碗,使他们累坏了。“该歇歇吧!”就歇下来。做陪娘的麻脸王嫂说不得,多给五魁丢眼色,五魁便提醒:“世道混乱,山路上会有土匪哩。 ”后生们偏放胆了勇敢说,“土匪怕什么?不怕。 ”拔了近旁秋季看护庄稼的庵棚上的木杆去吆喝打狗。狗子遂不再是一个两个,每一个沟岔里都有来加盟者,于亢昂的唢呐声中发生了疯狂。跃细长黄瘦剪去了尾巴的身子在空中做弓状,或奓起腿来当众撒尿,甚或有一对尾与尾勾结了长长久久地受活在一处了。于是后生们就喊:“嗨,骚狗子!嗨,骚狗子! ”喊狗子,眼睛却看着五魁背上的人。五魁脸也红了,脚步停住,却没有放下背上的人。
背上的人是不能在路上沾土的。五魁懂得规矩,愤愤地说:“掌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们当然不像五魁。”后生们说,“我们背的是死物,越背越沉。五魁有能耐你一个人快活走吧。”
五魁脸已是火炭,说:“造孽哩,造孽哩。 ”但没办法,终是在前边的一块石头前将背褡靠着了。背褡一靠着,女人的身子明显地闪了一下,两只葱管似的手抓在他的肩上,五魁一身不自在,连脖子都一时僵硬了。
五魁明白,这些后生绝不是偷懒的痞子,往日的接亲,都是一路小跑着赶回去,恋那早备了的好烟吃、烈酒喝,今日如此全是为了他背着的这个女人。
当一串鞭炮响过,苟子坪的老姚捏着烟迎他们在厅
过,若一经进了柳家,这女人就不是能轻易见得到的了。后生们如此,他五魁还能这么近地接触她吗?所以五魁也就把背褡靠在石头上歇起来。
八月的太阳十分明亮,山路上刮着悠悠的风,风前的鸟皱着乱毛地叫,五魁觉得一切很美,平生第一次喜欢起眼前起伏连绵的山和山顶上如绳纠缠的小路。如果有宽敞的官道,花轿抬了,或者彩马骑了,五魁最多也是抬嫁妆的一个。五魁几乎要唱一唱,但一张嘴,咧着白生生的牙笑了。麻脸陪娘走近来很焦急地看着他,又折身后去打开了陪箱的黄铜锁子,取出了里边的核桃和枣子分给后生们吃。这些吃物原本准备给接嫁人路上吃的,但通常是由接嫁人自己动手,现在则由陪娘来招待,大家就知道麻脸人的意思了。
“天是不早了呢!”陪娘说。
“误不了夜里入洞房的。”后生们耍花嘴,“瞧这天气多好!”
“好天气……”
“哪还怕了土匪?”
“哪里怕了土匪!”陪娘不愿说不吉祥的话,“你们可以歇着,五魁才要累死了!”
“五魁才累不死的!”
五魁想的,真的累不死。他就觉得好笑了。这些后生是在嫉妒着他哩。当五魁一次一次做驮夫的差事,他们是使尽了嘲弄的,现在却羡慕不已了。他不知道背上的女人这阵在想着什么,一路上未听到说一句话。五魁没有真正实际地待过女人,揣猜不出昨日的中午,在娘家的院子里被人用丝线绞着额上的汗毛开脸,这女人是何等的心情,在这一步近于一步地去做妇人的路上又在想了什么呢?隔着薄薄的衣服,五魁能感觉到女人的心在跳着,知道这女人是有心计的人,多少女人在一路上要么偶尔地笑笑,要么一路地啼哭,她却全然没有。她一定也像陪娘一样着急吧,或者她是很会懂得自己的美
魁,驮背一回这女人,已经是福分了,是满足了!于是,五魁对于后生们没休没止的磨蹭有不满了。
“歇过了,快赶路吧!”他说。
后生们却在和陪娘耍嘴儿,他们虽然爱恋着那个可人,但新娘的丽质使他们只能喜悦和兴奋,而这种丽质又使他们逼退了那一份轻狂和妄胆,只是拿半老徐娘的陪娘作乐。他们说陪娘的漂亮,拔了坡上的野花让她插在鬓角。五魁扭头瞧着快活了的麻脸陪娘也乐了。
是的,陪娘在以往的冷遇里受到了后生们的夸耀忘记了自己的本色,如此标致的新人偏要这个麻脸做她的陪娘,分明是新人以丑衬美的心计所在了。或许,这并不是新人的用意,而她实在是美不可言,才使陪娘的脸如此地不光洁吗?五魁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他离开了石头,兀自背着新人立在那里,看太阳的光下他与背上的人影子叠合,盼望着她能说一句:这样你会累的。新人没说。但他知道她心里会说的,他的之所以自讨苦吃,
是要新人在以后的长长的日月里更能记忆着一个背驮过她的人。
天确实是不早了,但后生们仍在拖延着时间,似乎要待到如铜盆的太阳哐嚓一声坠下山去才肯接嫁到家,戏弄了陪娘之后,又用木棒将勾连的狗子从中间抬过来,竟抬到五魁的面前,取笑着抹了朱砂红脸的五魁,来偷窥五魁背上的人面桃花了。
五魁无奈扭身,背了新人碎步急走。
这一幕背上的女人其实也看到了。一脸羞怯,假装盯眼在前面的五魁头顶的发旋上了。
互魁感觉到发旋部痒痒的。在一背起女人上路,他的发旋部就不正常,先是害怕虽然洗净了头,可会有虱子从衣领里爬上去吗?即使不会有虱子,而那个发旋并不是单旋,是双旋,男的双旋拆房卖砖,女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呢?到后来,发旋部有悠悠的风,不知是自己紧张的灵魂如烟一样从那里出了窍去,还是女人鼻息的微
微热气,或者,是女人在轻轻为他吹拂了,她是会看见自己头上湿漉漉的汗水,不能贸然地动手来揩,便来为他送股凉风的吧。
这般想着的五魁,幻觉起自己真成了一匹良马,只被主人用手抚了一下鬃毛,便抖开四蹄翻碟般地奔驰。后边的后生果然再不磨蹭,背了嫁妆快步追上,唢呐吹奏得更是热烈。五魁还是走得飞快,脚步弹软若簧,在一起一跃中感受了女人也在背上起跃,两颗隐在衣服内的胖奶子正抵着他的后背,腾腾地将热量传递过来了。草丛里的蚂蚱纷纷从路边飞溅开去,却有一只蜜蜂紧追着他们。
“蜂,蜂!”女人突然地低声叫了。
蜜蜂正落在了五魁的发旋上。
听见女人的说话,五魁也放了大胆,并不腾出手来撵赶飞虫,喘着气说:“它是为你的香气来的。 ”但蜜蜂狠狠蜇了他,发旋部火辣辣的立时暴起一个包来。“五魁,蜇了包了!你疼吗?”
“不疼!”五魁说。
女人终于手指在口里蘸了唾沫涂在五魁的旋包上。
五魁永远要感激着那只蜜蜂了。蜜蜂是为女人的香气而来的,女人却把最好的香液涂抹在了自己的头上!对于一个下人,一个接嫁的驮夫,她竟会有这般疼爱之心,这就是对五魁的奖赏,也使五魁消失了活人的自卑,同时产生了一种可怕的邪念,倒希望在这路上突然地出现一群青面獠牙的土匪,他就再不必把这女人背到柳家去。就是背回柳家,也是为了逃避土匪而让他拐弯几条沟几面坡,走千山万水,直待他驮她驮够了,累得快要死去了。
是心之所想的结果,还是命中而定的缘分,苟子坪距鸡公寨仅剩下十五里的山道上,果然从乱草中跳出七八条白衣白裤的莽汉横在前面,麻脸陪娘尖锥锥叫起来:“白风寨!”
白风寨远鸡公寨六十里,原是一个下河人云集的大镇落。二十年前,从深山里迁来了一对夫妇,妇人年纪已迈,丈夫很精神,所带的四个孩子到了镇落,默默地开垦着山林中的几块洼田生活着。这丈夫的脾气十分暴躁,经常严厉地殴打他的孩子,竟有一次三个孩子炒吃了做种子的黄豆,即用了吆牛的皮鞭抽打,皮鞭也一截一截抽断了。做母亲的闻讯赶来,突然破口大骂道:“你就这么狠心吗?他们是我的儿子,你也是我的儿子,你在他们面前逞什么威风?! ”那丈夫听了妇人的话,立即呆了,遂即大声狂叫起来,一头撞死在栗子树上。消息传开,人们得知了这一对夫妇原是母子,他们就愤怒起来。这妇人为自己的失言而后悔,也为着自己的失去妇德和母德,虽然她当年在深山这样做是出于为了能与野兽和阴雨荆棘搏斗而生存下来的需要,但她还是被双腿缚上了一扇石磨,而脖子套上了绳索挂在栗子树干
甚至会从褡裢中掏出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讲明这是官府×××或豪富 ×××,但他却是不能允许在他的辖地有什么违了人伦的事体。他扬起枪来一个脆响击中了秋千上的夫人,血在蓝天上洒开,几乎把白云都要染红,美貌的夫人就从秋千上掉下来。他第一个走近去,将她的裤子为她穿好,系紧了裤带,再脱下自己的外衣再一次覆盖了夫人的下体后,因惯性还在摆动的秋千踏板磕中了他的后脑勺。
现在,他们停下来,挡住了去路,或许是心情不好而听到欢乐的唢呐而觉愤怒,或许是看见了接亲的队伍抬背了花花绿绿的丰富的嫁妆而生出贪婪,他们决定要逞威风了。此一时的山峁,因地壳的变动岩石裸露把层次竖起,形成一块一块零乱的黑点,云雾弥漫在山之沟壑,只将细路经过的这个瘦硬峁梁衬得像射过的一道光线。接亲的队列自是乱了,但仍强装叫喊:“大天白日抢劫吗?这可是鸡公寨的柳掌柜家的!”
拦道者听了,脸上露出笑容来,几乎是很潇洒地坐下来,脱下鞋倒其中的垫脚沙石了,有一个便以手做小动作向接亲人招呼,食指一勾一勾地,说:“过来,过来呀,让我听听柳家的源头有多大的?”
接亲的人没有过去,却还在说:“鸡公寨的八条沟都是柳家的,掌柜的小舅子在州城有官座的,今日柳家少爷成亲,大爷们是不是也去坐坐席面啊!”
那人说:“柳家是大掌柜那就好了,我们没工夫去坐席,可想这一点嫁妆柳家是不稀罕的吧?!”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贾平凹的写作厚重辽远,体量庞大,他苦心孤诣的乡土帝国,作为当代中国的现实回声,深具世界影响。他以一己之力,尽显乡土写作的超拔之志,既古朴,又现代。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小说是心灵悔悟者的告白。他的叙事果敢、坚决,同时又不失隐忍和温情。他冒犯现实,质询存在,正视人类内心的幽暗角落,而批判的锋芒却常常转向对爱和希望的肯定。他以宽恕化解怨恨,以敬畏体认谦卑,以信念让软弱者前行,以倾听良心里那细微的声音来抚慰受伤者的记忆。
——谢有顺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