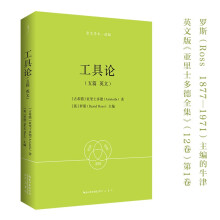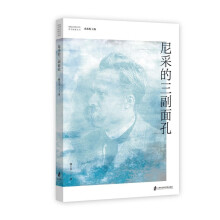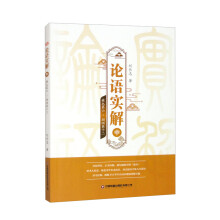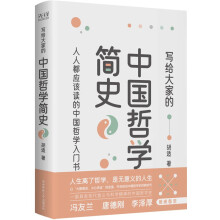《周作人与儒家思想的现代困境》:
周作人曾于四十年代初写过一篇名为《道德漫谈》的文章,其中说:“从前与老朋友谈天,讲到古来哲人诸子,总多恕周秦而非汉,或又恕汉而非宋,非敢开倒车而复古也,不知怎的总看出些儒家的矛盾,以为这大概是被后人弄坏的。世间常说孔孟是纯净的儒家,一误于汉而增加荒诞分子,再误于宋而转益严酷,我们也便是这样看法,虽然事实上并不很对,因为在孔孟书中那些矛盾也并不是没有。”ciJ此说既是周作人对于儒家传统之历史演进的看法,也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问题在于,原初儒家与后世儒家的区别在哪里?仅仅是汉儒多了些荒诞分子,宋儒转益严酷么?当然也不完全如此,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作人写道:“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来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就成为儒家衰微的原因。”在这里,他将儒家衰微的原因归结为法家与佛教的双重影响,但是此种见解似乎也处在变化之中,因为他还曾说过:“中国儒生汉以后道士化了,宋以后又加以禅和子化了,自己的生命早已无有,更何从得有血性与胸襟乎?”若照此说法,则法家的影响因素似乎又被剔除在外了。
不论说法如何变化,周作人的意思,始终是在强调,正统儒家的衰微乃肇因于外在思想之影响,以至于名存实亡,徒有皮囊,而无筋骨血肉,此等论说,与何炳松在《浙东学派溯源》中对儒家传统脉络的描画十分相像,惟何氏单独拈出程颐与浙东学派一线,以为正统儒家之遗存,而周作人的态度则更加悲观,直接认为儒家传统已经“衰微”了。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秦晖在《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一文中所提出的“法道互补”说法,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时代,尽管真正的儒家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血脉一直不绝如缕,到现在也仍然不失其光华。但实际上就整体而言,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互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而正如经济上因乱而管、因死而放,遂使‘死”乱’互为因果一样,在‘文化’上恶欲横流成为‘管’的理由,假话连台又成为‘放’的依据,于是假与恶也就互为因果,形成怪圈。“
确有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儒道互补“模式,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林语堂,在其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中,有一段这样的著名议论:“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2]若翻阅周作人的文集,类似的论述其实也可以找到,只不过比林语堂多添了一个“法家”:“道家前辈经验太深了,觉得世事无可为,法家的后生又太浅了,觉得大有可为,儒家却似经过忧患的壮年,他知道这人生不太可乐,也不是可以抛却不管了事的,只好尽力的去干了看,这即是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3]然则林语堂的论述是轻妙的、鉴赏式的,而周作人就没有这么乐观,他甚至觉得,在道家与法家的夹缝之中,真正的儒家只是一种微弱如同萤火的存在:“我常觉得中国儒家是一种化合物,根本的成分只有道家与法家,二者调和乃成为儒。而这化合往往未能完成,遂多现出本色,以法家为甚,如三从殆其明征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