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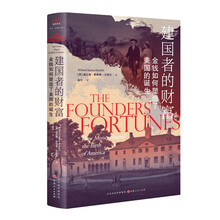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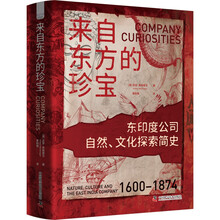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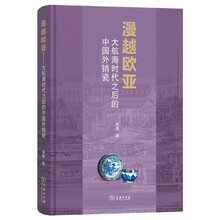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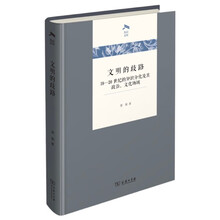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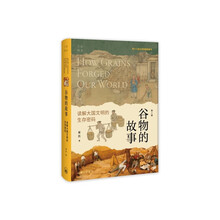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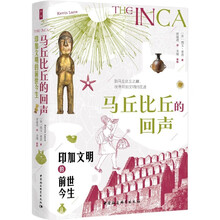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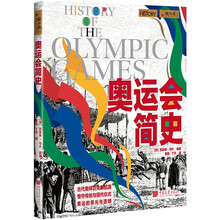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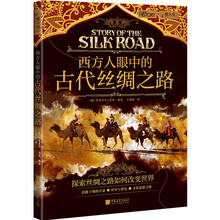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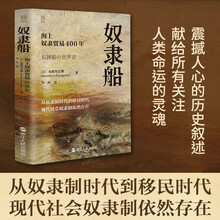
德国史学家兰克说:“法国的特点,是在各个世纪中不断地冲破合法的圈子。”千百年来,法国人以批判为荣,敢于思考,勇于表达,言为心声,以自由之言论对抗专制之暴力。
北大历史系教授郭华榕,精选了法兰西具有代表性的五十位历史人物,以扎实的史料、生动还原他们一生重要经历与思想演变,并着重介绍独特的言论和行为:
直抒胸臆如丹东 “我请求珍惜人们的鲜血”;
冒死反抗如卢韦-德-库弗雷“罗伯斯比尔,我就敢控告你!”;
冷眼观察如梅里美 “不当朝廷的奉承者”;
真诚反省如罗兰夫人 “自由女神,以你的名誉犯下了多少罪行!”
满怀激情如拉马丁 “人,作为奴隶,他生来便向往自由!”
奋起反抗如波蒂叶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千余年来的前贤先哲们关怀社会的思考、共赴国难的决心、对社会弊病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畅想,尽在这些惊世之言中一一体现,这次独特的探索使我们透过浪漫与激情的面具,得以还原历史长河中特立独行的法兰西人和法兰西灿烂文化的魅力。
人们通常将法兰西想象为一个浪漫与激情的国度,将巴黎视作彻夜歌舞、繁花似锦的大都城,法国人日常生活中随时荡漾着情爱……法兰西是心中永远的美景。这是追寻者设想的乌托邦的异化,是一种简单化和一厢情愿,或者旅游业为了招揽游客所需而着意夸张,实际上此类想法仅仅涉及事情的某些方面。就此问题而言还应看到,法国人自身的言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2—13世纪,以大学生为主的一个秘密团体“哥利亚德”(Goliards)宣称: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大革命之际,布瓦西—当格拉斯(Boissy dAnglas)在议会讲台上表示:“法兰西是世界上最好的民族”、“最开明的人民”、“巴黎是人类一切知识之家……世界的学校”。19世纪前期,政治家与史学家基佐(Guizot)认为“法国是文明最完美、最有感染力的国家……”1871年,巴黎公社委员德勒克吕兹(Delescluze)在公告中指出:“法兰西是一切革命之母。”这些人的爱国热情可以理解,然而对于法兰西或巴黎,需要较久的生活、冷静的观察、辩证的思考。法兰西或巴黎,那里的人与事,都是复杂的历史的产物,都有复杂的现状。过去,传说在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e),有一条小小的帕克托尔河(Pactole),河中漂流着黄金……传说,这只是旧日的传说而已!传说,有时是幻想的变种,翘首构思的空中楼阁,人们从中追寻着,甚至享受着自己的快乐与“快乐”。毕竟,塞纳河里从未涌现黄金波浪,却曾有造反者们的鲜血随水逝去。
在法兰西,可以找到许多著名的风景,如巴黎、马赛、博纳……卢瓦尔河畔的城堡、布尔戈尼的山峦、罗纳河中的水湾……它们都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但令笔者深受感动的是如此景色:农舍、牛群、坡地上无际的绿茵,草野中零星地绽放着鲜红的丽春花(coquelicot,又名虞美人)……见到此景,容易让人流连忘返。人和大自然的共同努力,匠心独运与鬼斧神工,在地球上、人世间创造了如此诱人的田畴……当我们经历了柏油路、水泥楼、交通堵塞、漫天雾霾等世界性的“大城市病”之后,那翠绿青葱中猩红点缀的景致显得令人神往。
法兰西的浪漫和激情不断诱发出感人的爱情,如罗兰夫妇、拿破仑与瓦勒弗斯卡、巴尔扎克与韩斯卡、乔治·桑与缪塞或肖邦,有时他们给后人以情大如天、揪心断肠的印象。同时,法兰西人的爱情故事中,经常难免过度的冲动、迅速的分合聚散,地动山摇与顷刻崩溃几乎彼此渗透互相呼应,而且这一切多是诚挚的、认真的。就笔者有限的知识范围而言,激动人心的爱情有如孔多塞(Condorcet)夫妇。为了躲避断头之祸,无辜的他被迫隐藏在巴黎市区。她在郊区竭力工作,冒着生命危险无数次含泪潜入巴黎城里,给孔多塞以物质支持和精神温暖,患难与共,生死相交,感人至深……为了爱情,人们如此独特地奉献,而那被诗人们歌颂至极的爱神,她为何见死不救?在断头台的面前,她未能拯救受难者当中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国际史学界较多人认为,1793—1794年山岳派专政(另称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时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约30万人,被判处死刑者16594人,未经判决与死在狱中者约4万人。被判处死刑者84%属于第三等级(其中25%资产者、28%农民、31%“无套裤汉”)、8.5%贵族、6.5%教士。有关数据至今无法说明其中无辜者的数字或比例。无辜的受害者远不止三五个、十个百个……即将身首异处的他们曾对爱神翘首期盼、望眼欲穿!在那情爱容易萌发却艰难持久的国度,孔多塞们的爱情显然引人注目。
我们看到,在绚丽的景色和真挚的爱情之外,还有更多的、更加辽阔的法兰西!有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劳动、军事、外交的法兰西。有巴黎的法兰西与外省的法兰西!尤其特立独行的法兰西!
浪漫激情、迷人景象、生死情爱,这一切都显示出法兰西的巨大的活力。我们经常见到实实在在的异峰突起!那里,有许多人勇敢地对社会、对生活进行思考……那里,既有血与火的碰撞,也有思想奔放的展示。鲜血与烈火磨炼了法国人,帮助他们坚持民族的特性,并在世界上保持显著的地位。思考者们的智慧如同溪水,仓促汹涌地或巧妙曲折地独自奔流,汇集成一条令世人瞩目的大江,法兰西一直在独立地思索着、行动着……
世界上,不少异国人士钟爱法兰西,甚至眷恋着法兰西!如此做法具有充分的理由,这往往是由于法兰西的令世人赞叹的独特性。人们容易受到它的独特性的束缚,然而这亦有好或坏、恰当或过度、适时或违时。独立特征对于人们的束缚,导致过度陶醉、身心迷惑,距离迷信或许仅有一步之遥,而一旦跨过了这个红线,收脚回身退到冷静思索的境界,可能十分艰难!拿破仑曾经指出:“从伟大到愚蠢,仅差一步。”人类的认识史,不断提供如此精神演化的例证。
早已有人批评法国人的性格。例如,马克思认为:“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一个阶级都是政治的理想主义者。”17世纪初,德·孔代(Condé)亲王表示:“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同德·吉斯公爵肝胆相照,因为我们都是法国人。今天我们信誓旦旦,明日我们就会矢口否认……天主造就了我们这种法国人,我们注定将永远疲于奔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坦然承认:“任何民族都不像法国人这样老是有始无终,工作才完成一半就改变计划……法国人总是心血来潮,不能坚持某一种意见。他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是使对立的东西混淆起来的中间人物。”现代史学家瑟尼奥博斯(Seignobos)如此描绘:“法国人喜欢说话,并且口语很流利,能够深思熟虑。”“他们更适宜于个人工作,而不宜于集体经营。”
一句精辟的话语,可能使说话者载入史册,如果它代表了人心的渴求、群体的前途、社会的趋向,或者是这一切的反面,背道而驰,甚至乱杀无辜……无论正与反,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它们都应该包含明确的独立性。法兰西人的可贵品质在于:不愿意唯马首是瞻、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突出地表现了法兰西式的政治尖锐性!笔者在本书中关注的不是对于人物的全面评价以及他一生的思想演变,而着重介绍他们独特的言论和行为。无论如何,这些法国人发挥个性,单枪匹马或统领人群,瞄准对手,刺激着社会,造成各种后果。也许正是由于这些言行,他们成为已经消失的社会生活在其他方面的亮点。法兰西经历了它的若干胜利的高峰和失败的低谷,走到当代,还将走向未来……我们关注它,并非将要竹篮打水一场空。“武装起来,公民们!”(《马赛曲》)与“勇敢,勇敢,再勇敢!”(丹东)的豪言壮语,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难当头之时,给我们以鼓舞。
此外,乔布斯曾说:“向那些疯狂、特立独行、想法与众不同的家伙们致敬。或许在一些人看来,他们是疯子,但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此话有一定的道理。一种新的思考,通常背离社会的流行趋势,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思考者面临着人们的不理解,甚至社会的阻力,如强势拥有者的歧视、批判、迫害。但是,几经曲折,最后获胜的、占优势的总是新生的事物!
从总体观察,人们具有与挥洒着自己的个性,于是汇集了、融合成了整个法兰西的一种独特性。关于它的独特性的形成,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难题,有待国际学术界的继续探讨。或许,风物各异的大自然、独立耕耘的农业、寻求个性的文化、反复折腾的国难……铸造了这样的特性。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曾经指出:“法国的特点,是在各个世纪中不断地冲破合法的圈子。”面对法兰西的错综复杂,笔者设想:如果由人物开始考察,集中关注他们的独立思想与行动,尤其他们关怀社会的思考、共赴国难的言行、对于社会弊病的批判、关于法兰西未来的畅想……如此探索也许将使我们能够穿过那浪漫无边与激情澎湃的雾霭,撇开感人的常态,找到一种比较新颖的实在的感觉。无疑,这不应写成一篇篇学术论文,而是通过人物与其言论的某些勾勒,指出他们的独到之处,仅此而已。笔者在写作中,已经感到实现这个愿望之不易。既然如此,应该学习法兰西文明的精神,勇敢地秉笔直书。这些就是笔者奉献此书的想法,如果能够容许这样的设想,敬请读者与专家诸君,浏览这一册或许正握在你手中的小书。不当之处,诚恳地请求指正,笔者唯有深深的谢意!同时,衷心感谢出版社的有关人士!
独立思考的法兰西,爱你真不容易!
请听高卢雄鸡的独自啼唱!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