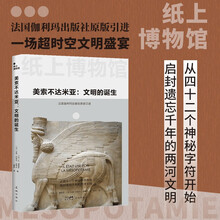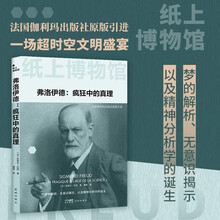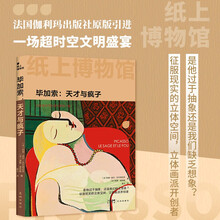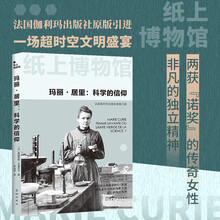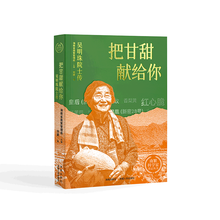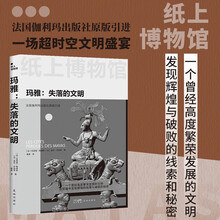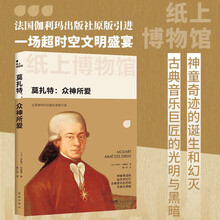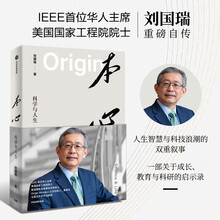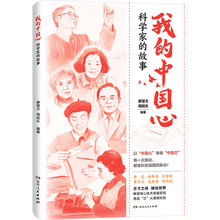《师表 回忆谢希德/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百年中国记忆》:
一段珍贵的回忆——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
谢希德
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丈夫曹天钦在各自的党支部不约而同地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本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要邀请曹天钦来参加,后来得知就是在同一个下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的党支部也要讨论天钦的入党问题。这对我们二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从此我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立志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的同志。当天我恨不得要立刻飞回家。到家后我们交流了各自支部大会的情况,对我们所提的意见。我们都感到很兴奋,认为能被接纳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感到很光荣,但是也都觉得还很不够标准,只好在今后不断努力。这种新党员的思想一直持续到1982年去北京开党的十二大的途中,国栋同志提醒我入党已有26年。我才意识到不能再以新党员自居了。当然在老同志面前,我永远是新的。
在那难忘的一天的晚饭后。住在楼下的李林和邹承鲁给我们开了一个祝贺的晚会。张友端和陈瑞铭也参加了。他们都是天钦在英国的同学,当时都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现在他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明党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知识分子从党外人士转变为共产党员都经过了一段各自不同的历程。曹天钦已于1995年1月8日离开人世,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写下我们二人如何得到党的关怀走上革命之路,作为献给党的七十五周年的一份心意。
我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天钦则早生一年。我们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代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仅在历史书上读到令人气愤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史实和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亲自体验到九一八、“一·二八”后在当时的北平日本宪兵的耀武扬威的气焰。家庭给我们的教育是好好念书,知识总是有用的。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我也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在1937年夏离开了当时的北平,先后到武汉和长沙,1938年夏在长沙福湘女中毕业后患股关节结核,卧病贵阳,休学达4年之久。曹天钦中学毕业后入了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的化学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日本统治下还能勉强苟安。他仍怀着“科学救国”的美梦,在给我的信中,除去鼓励我安心养病外,还不时寄给我他课外阅读的读书心得,或是假期在工厂实习的一些报告的点滴,当时他希望可以通过献身化学来救中国。1940年左右他和同学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乃和一些同学于1941年春天离开北平南下,先到上海栖身于当时的租界,后分两批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抗战后方。他选择了走北路,经开封到达西安,参加了新西兰友人路易·爱黎的工业合作运动,在当时陕西凤县双石铺的综合工业研究所作技正。分析一些矿石。次年他又转到在兰州的皮革合作社任经理。他的以化学工业救国的愿望,在这一段工作得到部分的满足。但他的确又不满足于留在兰州。他的大哥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离开学校到解放区,这对曹天钦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到达双石铺工作的那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日交战,燕京大学被迫在北平关门,不久迁到成都华西坝复校。曹天钦认为还是应该完成大学的学业,于1943年到成都继续攻读。当时抗战已6年,在成都就读的一些离乡背井的学生,生活都很困难。有些人生了肺病,也有人因此不幸身亡。和他同时离开北平的同学,有些人奔向解放区。我们虽未走向革命之路。但也都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心之所向是很清楚的,很羡慕那些朋友的决心。
毕业前夕,曹天钦遇到了重要抉择,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成都攻读研究生?当时我已病愈,在位于闽西长汀的厦门大学就读。他怕去解放区后,和我见面将更遥遥无期。正在进行思想斗争,通过友人介绍,他被聘到位于重庆由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领导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该馆为在抗战后方的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提供科研用药品和书籍。他随李约瑟夫妇辗转旅行于祖国的西南和西北。一方面协助李约瑟为写中国科学史收集材料,一方面也了解一些大学和研究单位科研的情况。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不少科学工作者还是努力在工作,曹天钦看了非常受感动。这些科学家的工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6年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出国前他到长汀去看我,我们订了婚。由于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去英国的交通还很不正常,没有定期的轮船或飞机。他被迫在南京和上海的英国文化委员会边工作边等待。当时我也从厦门大学毕业,来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后又到上海沪江大学工作。因此在他出国之前,我们又先后在南京和上海重聚。没想到这一别又是6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