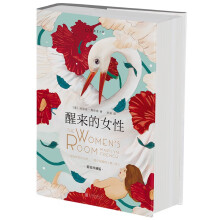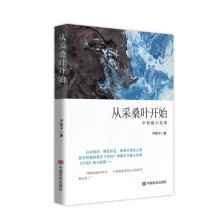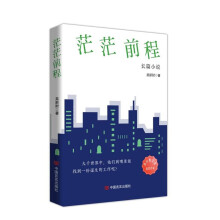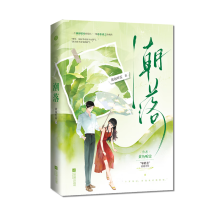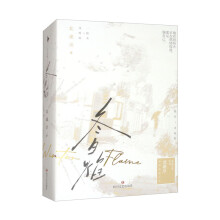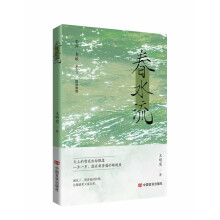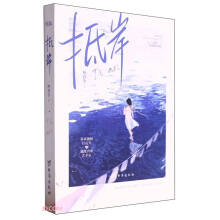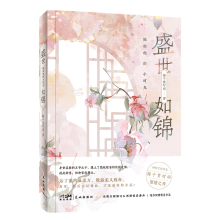第一章十年前的那个我
她,还没有来……
如果世上有一个地方曾让我魂牵梦萦,那便是这里;如果世上有一个地方曾让我发誓永不再涉足,那仍是这里:外赫布里底群岛的乌伊格湾。然而,我违背了誓言。
凯尼斯海浪不时地触摸着半月形的海岸线,弧形的潮水背后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无尽的循环。
和十年前一样,我又站在了这片白色的沙滩上,用鹅卵石拼摆出“BITL”的字样,静看着潮起潮落。星空依然晶透,海风依然拂面,甚至连空气的味道都不曾改变,只是……此刻,她并没在我的身边。
有时,我总会隐约地感觉到时间里有面镜子,时不时地让我看到曾经的自己。就像不远处的那对情侣,手牵着手,温馨、惬意,这画面太过熟悉。“曾经、镜子、画面?”不曾想,一到这里,我的情绪竟被这些怀旧词汇侵蚀了。其实,我并不喜欢怀旧,因为那是上了年纪的人的嗜好;可我又总喜欢写日记,因为这是一个绝对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会被人夺走,也不会被人左右。在心理学里,这叫“暗合矛盾行为”,这么“高端”的词汇是我从一位老人那里学来的,大体意思好像是“表层意识里的事物,实际在潜意识里是被接受的;当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潜意识会逐渐浮变成表层意识的行为”。那老人曾问我会不会常去看自己的日记,他说这是判断我是不是这种“矛盾体质”的主要依据,而我撒了谎。其实,即使是现在,这本日记仍然陪在我的身边。
日记本很厚实,但不平整,里层夹贴着很多便笺页,有随笔、有照片,这让它看起来更像个饱满的汉堡。翻着手上这件浮肿的东西,潦草、随性且杂乱无章,就像我那青葱岁月一样纠结、热情且茫无头绪。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自打记事起就没见过母亲的样子,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从这点上判断,母亲肯定是活着离开我们的……随着慢慢懂事,我对母亲的好奇与日俱增,可是关于她的故事版本却很多。有人说,她是因为父母反对,不得已才离开的;也有人说,她是因为和我爸性格不合而离婚的;还有人说,她是因为我爸没本事而“弃暗投明”去了。可无论版本有多“狗血”,作为第一当事人:我的父亲,却始终保持沉默。我记得很清楚,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父亲只提过母亲三次,而且都是在醉酒之后,一次哭着,两次笑着,含糊其辞,语无伦次。但无论孰是孰非,她离开了我且从没回来看过我,这是事实。因此,“母亲”这个重要的称谓在我心里成了疑问词。不过,久而久之,这个曾经的最大悬案在我心里逐渐失去了分量,现在它和一本普通悬疑小说的结局没什么区别。
“女人是什么?”那时,我对这个问题的好奇要远远高于“我母亲是谁?”。父亲那三次的又哭又笑是激发我好奇心的主要原因。堂堂一米九三的大汉竟然会有孩子般的失控,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魔力?当时我十四岁。从那时起,我开始尝试着去“认识”女人,这听起来很滑稽,却是事实。而此前,我眼中的女人,除了去卫生间时所走的方向和我不同,其他并无差别。在我接触的女人中,大多数是女孩儿,也就是我的同学。成年女性中接触最多的是我的班主任:一位六十二岁的老太太。通常来说,她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因为口碑好,教学能力强,被校方返聘了回来。这一点我必须承认,她的确对我很好。其实我认识的女性里,无论成年与否都对我挺好。逐渐地,我的意识里得出了一个“简洁而烂漫”的结论:“女人,好”。但不管怎样,很长时间里,这个结论让我在面对“女人”时保持了正能量。这对有单亲经历的孩子来说实属不易。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好”叫女人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