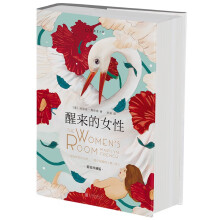一
我拉着沉重的旅行箱,徘徊在伯恩茅斯的大街上,脸上流淌着一个18岁中国妹子无助的泪水。我不知道这条街叫什么名字,中秋湿漉漉的晚风吹拂着陌生的建筑,吹拂着穿梭于街道上所有的Yellowbuses和Redbuses(注:两家公司的公交车,黄色的通往郊外,红色的跑市内),行色匆匆的蓝眼睛白皮肤的男人女人们从我身边闪过,我却无法或者有胆量向他们喊出“Hello”,因为,一旦某个人被我叫停下来,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表述我要找酒店暂住或者租房子。小留学生英语怎么说,酒店怎么说,租房子又怎么表达,我统统不知道。我只能马马虎虎地说清“IamfromChina(我是一个中国人)”!
那个时候,我看着渐渐落下去的夕阳,看着街道两侧逐渐亮起的灯光—那夕阳、那灯光和家乡的夕阳灯光有什么分别吗?我开始怀恨苏护士和夏编辑了。都是因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固执,才使我落得如此狼狈漂泊的下场。唉!我的父母亲!大人们啊!我在国内考不上好大学甚至普通大学又怎样?考不上好大学就一定没有工作可做吗?我会饿死吗?为什么非要学着人家有钱人,东拼西凑地把我变成一个“小留”呢?镀了金就一定能得到好工作吗?何况我心里对自己是否能够或者有能力镀得真金一直持怀疑的态度。我也开始怀恨那家代办留学的中介公司了,是他们把什么都说得好得不能再好,为了赞誉伯恩茅斯,甚至不惜贬损我们人间天堂苏杭,还说什伯恩茅斯是全世界学习英语最好的地方。哼哼!最好的地方怎么连“小留”的住宿都不能提供?
肚子叽里咕噜地不停向我讨要食物,是呀,十多个小时了,我还仅仅在飞机上简单用了一点航班赠送的小吃。但是,我却没有一点食欲,我遭遇着18年来前所未有的恐慌,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空气,陌生的面孔,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如果是在家乡,即便我身上没有一分钱,我也决不会沦落到露宿街头。可是现在,现在我的行李箱里虽然藏有足够的现金,中外两用贷记卡上更是存有足够的欧元,但我能够手擎着钞票,满大街地叫嚷“我要住宿—我要住
宿—我要住宿”吗?当然不能。因为我相信,即便我那样做了,也不会有谁能听懂,更别奢望有人会帮助我,充其量会引来一大群好事的伯恩茅斯人围观,那些人会耸肩摇头,相互低语或大声嘲笑。虽然不能说我此刻代表中国,但我就是不能任由他人鄙视和嘲笑!
我止住了眼泪,因为我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不过,这不但没使我恐慌,反而让我陡地增添了精神,来了斗志。英国是法律非常严谨的国家,何况此处应该是伯恩茅斯市的中心街道,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地走过,街道的斜对面就有一个手持警棍的警察,如果我高声喊“Help(帮助)”,他一准儿能够听到,我不信有谁敢这么胆大妄为地拦路抢劫。我索性停下来,转过身,干脆瞪起眼睛迎视着那个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男孩。他好像跟了我很久了,也许打我从伯恩茅斯语言学院一出来,他就盯上了我,一直在跟随我。男孩一脸纯真的憨厚相,哪儿哪儿都不像个邪恶之徒。见我怒视他,他并不躲开我的目光,干脆直接冲我走过来,一直来到我近前。我看了看街对面的警察,意在提示他也看看那里。他果真看了看那里,但很快就又把脑袋转回来,冲我耸了耸肩歪歪头,忽然用手掌一按自己的胸口,说:“你好!我……我叫Andy,不是坏人……”他又把另一只手抬起来指着我,“你……不用……害怕,你……中国……”
那一刻,我的眼泪又流出来了,不过不再是委屈和无助,是激动和庆幸。啊,是的,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在离家万里的英国南部,这样一座边陲小城,居然能让我碰到一个会说一点汉语的伯恩茅斯男孩。我的幸运还不仅如此,原来,这个叫Andy的男孩,他们家就是一个专门给各国留学生提供饮食起居的服务家庭,英国人管这样的家庭叫Stayhome(寄宿家庭)。
二
来到伯恩茅斯的第一天我几乎整夜无眠,并非因为想家。不要把我看成普通的娇滴滴的女孩子,事实上我一点也不留恋苏护士和夏编辑,尤其是前者—那个我称其为母亲或者妈妈的女人,她简直就是那个家里不折不扣的君主。我每天放学回来,她都要以怀疑的眼光检查我的听课记录,检查课堂练习和作业,每每我刚一进家,甚至还不等我放下书包,她就追着我催我洗脚洗脸,嘴里嘟嘟囔囔地吵嚷着:“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想看一眼电视放松放松紧张的神经,她立刻就会不高兴。我累了困了,刚没忍住打个盹儿,她立刻就批评我缺乏毅力,少骨气。我考进校前二百,她逼我进一百;我考进校前一百,她又逼我进五十。如果能拿到二本,她盼我拿一本,等我能拿到一本,她又督促我拿国家重点,拿清华北大……你们说,像这样的君主,我如何能满足得了?既然满足不了,哼哼……高二以来,我的成绩偏偏就每况愈下,节节败退。在苏护士可能预感到我连最普通的大学恐怕都无望的时候,她突然一个决定,毫无商量余地地就把我变成了一个“小留”。
我往夏编辑的手机上发了条短信:平安,勿念。
Andy长时间地逗留在我的房间里,这也许背离了英国人的习俗,但我并不讨厌他。Andy不是个聪明的男孩,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比一般男孩的智力好像还要稍差一些,不过也许正是这稍差一些,我才不讨厌他,才觉得他有点安全而可爱。Andy天性纯良,性格外向,非常喜欢说笑,尽管语言表达能力较差,但他非常好学,尤其对我们的汉语兴趣浓厚。我从他整整一个晚上的零乱的汉语字词间分析了解到,他20岁了,留过两级,也在那所语言学院里读高二。这样讲,我们应该算是同学了。据他津津有味的介绍,伯恩茅斯确实是世界上学习英语的最佳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的从小学五六年级到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涌到这里求学,也因此,学校才暂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人的住宿需求。
Bournemouth(伯恩茅斯)属于海滨城市,而在英国南部沿海一带,叫这个mouth(口)那个mouth(口)的城市特别多,反正不是在大河入海口附近,就是临近海湾口,所以才有这样的称呼。这座城市并不大,大约有十七八万人,和英国其他城市一样整洁有序,只是现代气息似乎更多一些,少有古旧建筑,享有世界一流度假胜地及“鲜花之都”的美誉。
伯恩茅斯依伯恩河入海处而建。
Andy家宽敞的三层别墅就坐落在伯恩河边,拉开窗,波光粼粼的河水尽收眼底,水面上倒映的五颜六色的万家灯火,不时被急急驶过的大大小小的油轮或客船所击碎,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海水的腥湿气息,混合着别墅前的花园里不断散发的幽香。
Andy离开时已是下半夜,经过长时间的奔波,虽然我的脸上已有倦容,但却丝毫没有困意。这没办法,谁叫我在干燥且浮尘肆虐的家乡,从来观赏不到如此洁净、水天一色的城市夜景呢?我久久地站在窗边不愿离去,贪婪地呼吸着腥腻腻的湿润的空气,瞪大眼睛仔细欣赏夜幕下伯恩茅斯的景致。伯恩茅斯格外明亮的星空令我陶醉,渡轮驶过,伯恩河时断时续的涛声更给我梦境般的幻想,使我想到伯恩河边长大的男孩Andy。他以后会和我发生故事吗?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三
在伯恩茅斯的第一个早晨,我被一阵紧过一阵的敲门声惊醒。我骨碌一下坐起来。窗外的太阳已升至半空,这哪里还是早晨?难道手机的闹钟没响?我抓起手机,上面赫然显示着已是
17点多。中秋时节,此刻应该是下午临近黄昏才对,莫非我是在梦境当中?可是敲门声分明越来越激烈,我忽然清醒了。啊,不对,这不是在中国,这是伯恩茅斯啊。糟糕,我的手机竟忘了调整,还是北京时间,伯恩茅斯此刻应该已是上午9点多了。今天是我上语言学院寄宿高中的第一天,我怎么连这么重要的事都给耽搁了?真是该死!我赶紧穿上衣服,一面喊着来了来了,一面冲门口跑去。
门外站着的居然是Andy。
Andy真是个热心的好男孩!
我一路上跟在Andy身后,默默地在心里重复着“Thanks”,默默地走,默默地跟着他登一辆经过语言学院的Yellowbus(黄色公交车),默默地听他嘴里不停地蹦着生硬的汉语。“以后,你,没,搬到,学校,之前,我,每天,都,负责,接送你,反正,我们,也是,同路。”我不知道Andy为什么如此关心我,从一个有点傻的异国男孩的眼神里,我暂时还看不出任何异样来,我姑且认为,这大概是一个小房东要和他家的房客建立和谐友好的关系吧,毕竟
我是他主动拉来的房客,我给他家增加了不少收入嘛。
“小留”寄宿高中班均设在三楼,宽宽的楼道里十分洁净,但并不安静,就像家乡学校课间的样子,老远就能听到喧哗声。Andy把我带到三楼的楼梯口,为我指点了我们班的教室,说了声“放学,等我”,就一溜小跑地跟他道别了。我怯怯地向IB2-4走过去,不知道迟到了要不要像在国内那样喊报告。我想象着也许陌生老师的蓝眼睛会冲我大大地瞪起来,先给我来个下马威。那扇鹅黄色的门大敞四开,我停在门口,里面似乎没上课,十来个人围在教室的中间,正七嘴八舌地交谈着,可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他们交谈所使用的语言,居然是我全部能够听懂的汉语普通话。我看看他们的容貌—黑头发,黄脸皮,这分明都是中国人嘛。一瞬间,我竟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又回到了暑假前的母校,可再看看黑板上的大大的红色标语—Welcomenewstudents(欢迎新同学)!还有两个黑人和两个棕褐色皮肤的人呆头呆脑地站在四周,我这才敢确定,IB2-4肯定就是我即将求学一年的班集体。
说来真是滑稽透顶,又万般无奈,我万里迢迢地跑来英国,来到一个还不如家乡城市大的伯恩茅斯,而且苏护士和夏编辑一年要花掉30余万元人民币,可谓巨额投资,是何等的盼女成凤!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他们的宝贝女儿—夏米苏所在的B2-4班,共18名留学生,其中有14人竟是我们大汉民族同胞,十足的中国“长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大人们啊,如果你们了解到,现如今每年有大约二十万的中国“小留”钻到世界各地,你们
还会那么趋之若鹜、义无反顾地让自己的孩子远渡重洋吗?事实上,一踏上“小留”的道路,就注定我们中有许多人一年后将成为任人嘲笑的一无是处的“海带”(海归待业人员)。这真让家长们始料不及呀。
我是被一个绰号叫“汉奸”的男孩拉进教室的。
“汉奸”是闽北人,他这个绰号是今天早晨一长春妹子宋戴儿给起的。我不知道宋戴儿为什么给他起了个这么难听的绰号,刚一见面我也不好追问宋戴儿,但我感觉闽北“汉奸”对我还算蛮好的,是他最先发现了怯怯地站在门口的我。他先是吹了声口哨,接着就老朋友一样喊出了我的名字。“夏米苏,你们看,夏米苏!我们的最后一个有缘人终于姗姗而来了。”我看见“汉奸”噌的一下敏捷地跃过桌子,眨眼间冲到了我面前,我还在愕然中,就被他一把拉住,不由分说直接将我拉进了人堆里。不要奇怪,先来的人自然能看
到IB2-4班的花名册,自然就记下了迟迟不到的同样fromChina(来自中国)的夏米苏。我窘迫地不知该面对哪一张脸,或者哪一张嘴,十三个同胞几乎同时向我发问。“夏米苏,快说说,说说,你是哪个省的,看看与谁最近。”正犹豫间,我忽然发现了一个人,这
个人就坐在我身侧,他的脸酷似Andy,白白的,鼻子高高的,眼睛蓝蓝的,是深邃而透明的蓝。那双蓝汪汪的大眼睛忽然冲我笑了一下,他站起来,友好地用力抓住我的手,他看上去好像比我们大几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