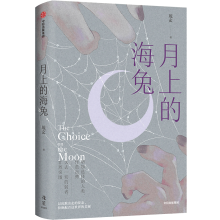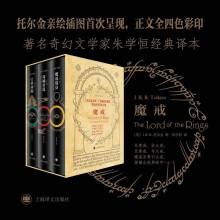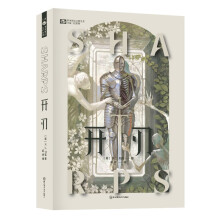《字造》:
一
男孩躺在树林里做梦的时候,阳光越过密集的树叶,直射在他脸上,形成一些闪烁不定的斑影,而光影就此进入梦里,变成水面上的波纹。他看见自己以鱼的姿势在水里游走,向一切水中的事物致敬。他向其他鱼问候,向水底的虾和蟹问候,甚至向浮动在泥岸边的螺蛳群问候。他内心充满巨大的喜悦。他是自由的,而且跟这世界无限友好。
自从两岁记事起,他就沉湎于这种白日梦幻之中,每天早晨,他溜进屋后的杂树林里,躺在一棵开花的老槐树下,周身包裹着阳光,就像穿上一件用光的纤维织成的袍子,睡意随即像树根那样从头脑、胸口、腹部和四肢一直延伸下去,他睡得仿佛石化了一样,直到黄昏被外婆叫醒。外婆是一名女巫,只有她能走进他的梦境,并把他拽出来,用树枝抽打他的屁股,把他赶回家去。
“该吃饭了,我的小畜生。”外婆咩咩地说,声音像颤抖的羊叫,“水里的鱼,已经在锅里等你了。”
男孩是个哑巴,嘴里天生就少了一根舌头,无法向外婆形容他在梦里的快乐。他抓住外婆的手叫了一下,外婆便笑了:“唉,你这小畜生,不是睡觉,就是拉屎。”男孩便欢快地跑到杂草丛里,拉了一泡臭气熏天的屎。完毕之后,他又欢快地叫了一声,看见茅屋上的烟囱,冒出了青灰色的炊烟。
他抓住两条蚯蚓当鞋带,它们就自己在草鞋的绳扣里穿来穿去,最后还打了个蝴蝶结,然后就静静地趴在草鞋上了。他穿着鞋跑进屋去,坐在火塘边,看见真的有条大嘴尖齿的鱼躺在陶盆里。越过热气腾腾的汤缶,一张秀丽的小脸,正在笑眯眯地望着他。那是他的表妹阿嚏。她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说:“小畜生今天在梦里干啥呀?”
男孩用手指指了一下鱼,又做出张嘴说话的样子。女孩说:“哦,我懂了,这条鱼刚才咬了你,所以你要把它吃掉。”她一脸坏笑地望着男孩。
男孩没有吃鱼,他很快吃光碗里的小米饭,然后去揪女孩的辫子,女孩也扔下筷子,在他手上轻咬了一口,留下一圈浅浅的印章式的牙印。他们开始在屋里嬉戏和打闹起来。这是他们每天必需的功课。外婆笑眯眯地望着绕膝的孙辈们,犹如望着歌谣里的世界。
男孩在女孩细长的辫子上打结。女孩在闪避中对男孩说:“颉,你对我那么凶,可我对你这么好,就连吃一只跳蚤,都要分你一条腿。”男孩大笑起来,向她伸出一根食指,意思是要分给她一个指头。女孩又说:“假如颉哥哥是条小狗狗呢,那么妹妹就是一根小骨头,让哥哥叼着跑东跑西。”
女孩接着说:“要是我们以后在一起了,我就让所有东西都到一起来,我要把我的鞋放到你的鞋里,把你的袜子放进我的袜子里,让衣服跟衣服、枕头跟枕头都成为夫妻,还有,我的手和颉的手也要成为夫妻。”颉听罢有些羞涩起来,伸手捂住了女孩的嘴。
女孩推开他的手,又把舌头伸进他的嘴里。颉含着女孩的小肉舌,好像含着一条温暖的小鱼,心想它是多么柔软,多么芬芳,津液里带着青草的香气。女孩说:“我们的嘴巴也要成为夫妻。”颉的脑袋有些发晕,他被这次亲嘴震撼了,仿佛掉进了外婆热气腾腾的浴盆。此后的许多年里,他都无法忘掉这个灵魂的初吻。
夜深之后,外婆和女孩都去睡了,颉便进入自己的另一个状态——开始在泥地上写画。夜晚的生物已经出动,狼在附近叫春,夜枭发出令人惊悚的笑声,饿虎则在远处山谷里咆哮。颉也发出了自己的童声号叫。他像一头小狼,坐在屋门前,背靠坚硬而冰凉的门板,开始在泥地上画符。这是外婆传授的一种技法,巫师们在作法时,会在芭蕉叶或高梁叶上,用点燃的碳条画出黑色神符,树叶随即燃烧起来,形成一些诡异的图形,又以灰烬的方式消失在空气中。
颉依照树的形状画了一个神符,又照鸟足的形状画了另一个。抹掉之后继续画第三个,就这样无限地画下去。他能够感觉到这些神符的能量,它们在被画出来的时候是会笑的,但在被抹除时,却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从笑到叹息只有一个瞬间。它们的生命如此短暂,令颉有些感伤起来。
早熟的哑巴男孩惘然想道,应该把这些笑声和叹息声都用罐子装起来,不让它们在巫术中死去。他的忧伤从指缝里流了出来,掉进了干枯的泥土。
但他还在不断重复这样的动作。日复一日,做梦和画符,这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事务。即便刮风和下雨,他都在这两个状态里摆动。表妹阿嚏有时会来恶作剧地加以干扰,她嬉笑着蒙住他的眼睛,玩弄他长在前额上的那块隆起的圆骨,拧他的耳朵,把一队肤色黑亮的蚂蚁送进他的衣领。颉在做梦时分是快乐的,在画符时分是忧伤的,只有在被阿嚏戏弄的时刻才是幸福的。他傻傻地笑着,被阿嚏身上的青草味儿弄得心醉神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