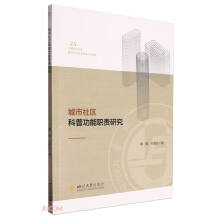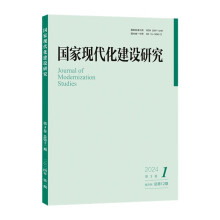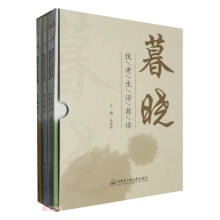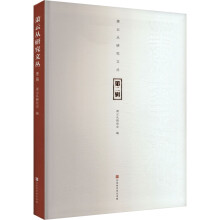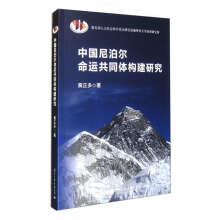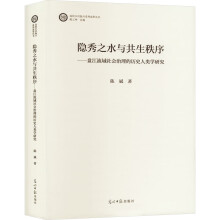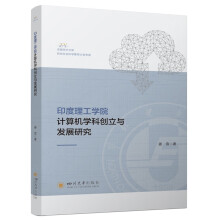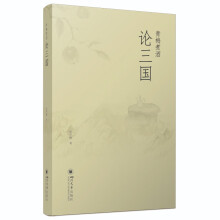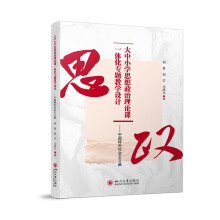1 启蒙
话说,1956年10月沃幸康呱呱坠地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双职工家庭。住址就是海曙区孝闻街黄岳巷21号,开始他“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清平生活。数年后,父母又给他添了一个妹妹,一家四口,生活平和淡然。
只是,随着国家市政建设与经济发展,原来的黄岳巷已是“销声匿迹",当年的风迹烟痕难觅,越趋远去。俨然“拂地西风起白门,几枝寒碧衬烟痕”,皆成了他幼稚年代的朦胧记忆。往年,沃幸康童时玩耍、嬉戏的地方,业已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到“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迹,气亦不识。”一个懵懂少年的儿时记忆,竞成逝水流年一个梦;甚至,成了沃幸康个人意义上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岳巷安在哉。
再说,提耳听命的沃幸康,经常随其痴迷戏曲的奶奶,出入演出场所,耳濡目染的听戏、看戏。无意间,他奶奶带他看戏,竟成就了沃幸康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戏曲启蒙,舞台记忆。画面感十足的戏曲人物,深深地吸引了“少年不谙世事"的沃幸康趋之若鹜,成了他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然,这个时候的沃幸康随其奶奶看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剧院,而是在一个简陋的戏场里上演。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之属,唱的江南地区的滩簧,一种曲艺。其实,古代戏曲史不分戏与曲,至于是戏与曲综合,那是现代综合舞台样式。
当年的剧场场景,它远不像今天现代化剧场的那般豪华。那是一个十分简易,粗陋的舞台;整个场子也不大,票价低廉1角3分钱。剧场大概可以坐上个二三百人左右的观众,座椅一般都是用毛竹子做出来的,观众入场不对号,大家按进场早晚择优而坐,特别有乡土气。
观众人座后,往往一边看戏,一边喝茶。这喝茶用的杯子,就可以放在前面椅背上,还有人不停地过来为观众续水,有的观众还可以悠闲地抽着烟。场内气氛可谓自由,也没有任何干涉。
其中,戏班在演出前等候观众时,还不停地敲打“开场锣鼓”。剧目开演中,台上演员在演,台下观众随意聊天、喝茶、嗑瓜子……这就是沃幸康奶奶带他常去看戏的场所,大约就在宁波当时的“西门口”那一带。这里,成为了少年时代沃幸康的观戏体验。他说场内气氛随意,还算安静。而地方戏曲,就在这样的不经意瞬间,将沃幸康击中,竟然成就他终身的一个托付,初衷不改。
这就是沃幸康意念中的戏园子,不奢华、不精致,却是如此的接地气。而潜影默化的戏曲舞台,才是一条很好的爱国爱乡教育。令“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人,有了“回家”的感觉——这就是家乡戏的文化魅力,戏曲本身就是纯粹的“兴观群怨”过程。
那些年的沃幸康,只有五六岁的模样,常常伴其嗜好戏曲的奶奶。她晚上没事,就喜欢去看戏。他便缠其左右,跟着一同出入剧场、茶肆,各类戏曲,环境使然地浸润其间,乐而忘返,从而有了“与戏剧的一次次地亲密接触”。而正是“这些年”的无意间,滋润着沃幸康的戏曲基因,且一发而不可收拾。“环境造人”是很有道理的,沃幸康就是一个鲜活的人文范本。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