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上的研究可上溯至鲁迅先生1927年在广州所作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1940年)一文,冯友兰先生的《论风流》(1944年)一文,都是较早的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鲁迅先生的研究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王瑶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书即深受其影响。此外,鲁迅先生提出的“魏晋风度”这一概念被后来研究者广泛接受。宗白华先生的文章对后世美学研究更是影响巨大,文中提出的诸多观点,成为中国美学研究的经典论述。这三篇文章我们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这里暂不展开。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界陆续出版了数本与本论题有所关联的研究著作,如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该书从时代思潮与文人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以历史分期将玄学分为正始、西晋、东晋三个时代,探讨了玄学思潮下相关士人所具有的心态及精神风貌,如将嵇康认定为“悲剧的典型”,将阮籍视为“苦闷的象征”。该书重在士人心态的研究,并开启了一条士人心态史的研究思路。宁稼雨的《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东方出版社,1992年),该书从魏晋门第观念、南北文化差异、人物品藻、魏晋学术思潮、魏晋人物个性、魏晋文艺、魏晋风俗等几个方面对魏晋风度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展示,其目标是“描述一幅活的魏晋文化风貌图”①,内容很为丰富,作者重在描述史实。范子烨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考察人物品藻,中篇论述魏晋清谈,下篇分析了嵇康、阮籍的游仙诗、《世说新语》的语言与人物、挽歌、啸等审美风尚,该书重在史料丰富,论述较为深入。宁稼雨的《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世说新语》为研究中心,从精神史的角度对魏晋士人人格进行了考察。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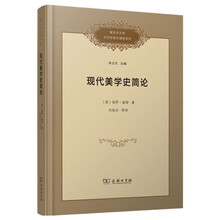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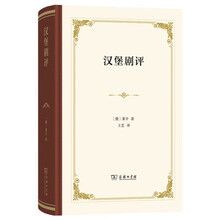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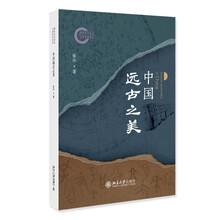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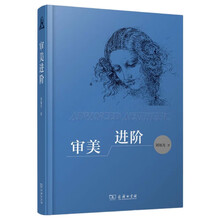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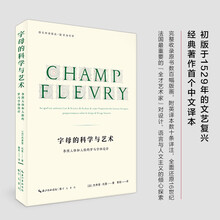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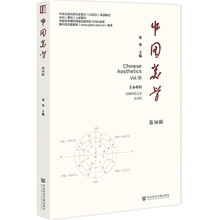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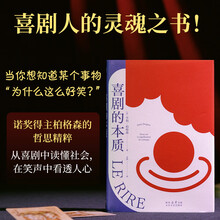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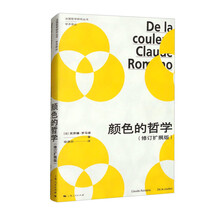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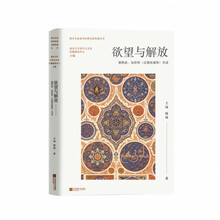
——鲁迅
真正风流底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底同情。
——冯友兰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宗白华
故顺《人物志》之品鉴才性,开出一美学境界,下转而为风流清谈之艺术境界的生活情调,遂使魏晋人一方面多有高贵的飘逸之气,另一方面美学境界中的贵贱雅俗之价值观亦成为评判人物之标准,而落实在现实上,其门第阶级观念亦很强。
——牟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