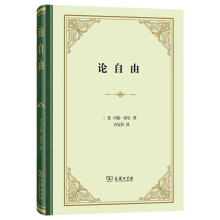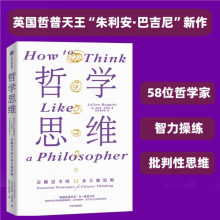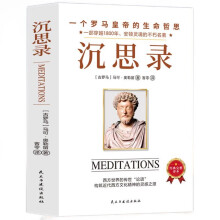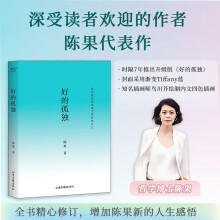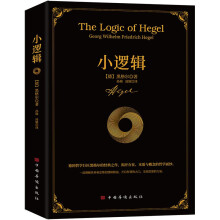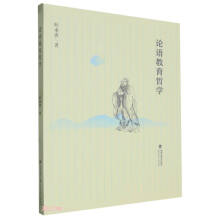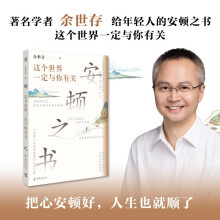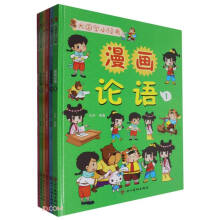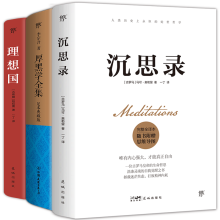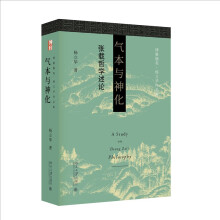结束这一子题时,海德格尔将合唱抒情诗人品达与箴言诗人赫拉克利特相提并论(比较前一子题将帕默尼德与赫拉克利特相提并论)。言下之意,从品达到索福克勒斯的诗作,“在”这一形而上学的终极沉思对象的古希腊语词源还没有变味——海德格尔似乎从尼采的教诲(柏拉图主义败坏了肃剧精神)中领悟到,柏拉图主义最终败坏的是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对“在”的理解。
接下来的第三子题为“在与思”(Seinund Denken),此节不仅是第四章、也是全书篇幅最长的一节,共62页,占全书三分之一强。海德格尔用这样多篇幅要说什么呢?扼要地讲,经过前面的铺垫,海德格尔试图站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和诗人)的“在”的理解这片土地上,推倒从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主义”大厦。
海德格尔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思?从柏拉图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都把“思”理解成逻辑(不妨比较胡塞尔对哲学的理解)。但如果回到古希腊先贤的源头(通过分析逻各斯的词源,尤其赫拉克利特论逻各斯与自然的关系),按海德格尔的精心谋篇和悉心解释,逻各斯(思)并非与逻辑相关,而是与自然相关。结论可想而知:自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误解或者说背离了自己的精神源头,对“在”的误解就发生在索福克勒斯之后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
随后的第四子题为“在与应当”(Seinund Sollen),篇幅也不长,仅9页。从子题的题目来看,此节要说的是形而上学(Sein)与实践哲学(Sollen)的关系——这也是“形而上学导论”的题中之义。然而,海德格尔在这一子题中首先攻击康德伦理学,然后指出,康德哲学的错误来自柏拉图,最后提到尼采毕生关心的虚无主义问题。这一节与全书第一章明显相呼应,其关联含义是:当今世界的大地沉沦、科学主义霸权和马克思主义势力都与康德伦理学相关,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具有形而上学的同质性,都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结下的怪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后果)。一言下之意,如今的哲学教授们一边批判现代性、一边膜拜康德,是再滑稽不过的事情。尽管如此,要找历史的真正罪人,海德格尔说,还得找到柏拉图头上。
从全书内在结构着眼,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线索:美国和苏联这两个现代利维坦是世界沉沦的表征,如此沉沦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有关,因此当理解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第一章);现代性的生活实践原则(伦理)由康德奠基,如此奠基依赖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第四章第4节),要彻底批判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开端(第四章第3节),就得回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之前;然而,回归路程艰难曲折,得通过苏格拉底之前的诗人如品达、索福克勒斯(第四章第1-2节),才有可能理解西方源头真正的形而上学。
结束全书时,海德格尔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诗人荷尔德林的几行诗句(值得想起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结尾)。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