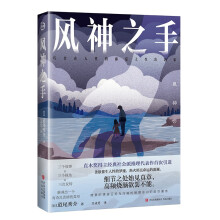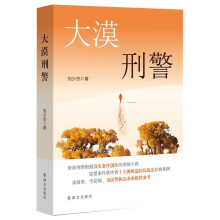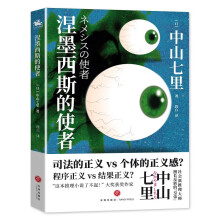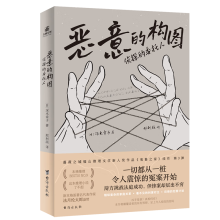摩托车怒吼着冲上山顶,骑手头上的护目镜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虽然已是早春时节,但仍然寒意逼人,骑手穿上了双层的皮外套,皮飞行帽的扣子紧紧地扣在下巴上。
他已经在路上走了三天,只有加油的时候才停到路边歇口气。摩托车座位两旁的挂包里鼓鼓囊囊地装着他精心准备的罐头食品。
入夜的时候,他从不在镇上投宿,而是把摩托车停在树丛里。这是辆全新的德国造“尊达普”K500型摩托车,有锃亮的金属车身和钢梁。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是买不起这辆车的.,但是如果这一趟能顺利走下来,不要说车子,更多的都能赚回来。他孤身一人躲在树林里,打开罐头喝着冷汤,寻思着未来的美妙图景。
他从地上捡来些树枝,准备把车精心地伪装起来。盖上树枝之前,他先细心地拂去真皮座椅和泪滴形的油箱上面的灰尘。如果发现一丝划痕,他就冲着上面吐一口唾沫,然后用袖子来回擦拭。
他席地而睡,身上就盖着一张油布,身旁没有温暖的火堆,甚至连抽根烟提提神都不行。烟味也许会暴露他的位置,他可不愿冒这个险。
有时,他会被旁边公路上隆隆行驶的波兰军用卡车惊醒。车子只是经过而已,很快就绝尘而去。
还有一次,他听见林子里有些动静,便坐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左轮枪,结果发现是一头牡鹿从距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经过,影影绰绰地看不见样子,而斑驳的树影仿佛都有了生命,让他惴惴不安。这之后,他彻夜未眠。童年时代的梦魇仍然折磨着他,周围好像潜伏着头上长着巨角的半人半兽的怪物,随时会向他发起进攻,他迫切地想离开这个国家。自从他越过德一波边境进入波兰之后,紧张的心情便没有舒缓过,虽然路上碰到的人对他熟视无睹。这不是他第一次踏上旅途,但经验告诉他,只有完成任务,重返自己熟悉的国家,恐惧和紧张才有可能消除。
第三天,他来到一个孤寂偏僻的边境检查站,穿过这里便是苏联的领土。检查站由一名波兰士兵和一名苏联士兵共同把守,看得出,两人之间语言并不通。士兵们从检查站里钻出来,对停在面前的摩托车赞不绝口。“尊达普!”他们异口同声地喊出这个名字,语气又热切又温柔,好像在呼唤爱人的呢称。骑手站在一旁,牙关紧闭一言不发,任由他们在摩托车上摸来摸去。
离开检查站几分钟后,骑手把车开到路边,摘下戴在头上的护目镜。公路上尘土飞扬,骑手脸上只剩下眼睛一圈还稍微干净些,此时,眼睛在其他部位皮肤的衬托下,像两轮圆圆的月亮。他抬手眺望面前连绵起伏的农田。田地刚刚被耕种过,泥土朗润,黑麦和大麦的种子沉睡其中。袅袅炊烟从农舍的烟囱里冒出来,石板铺就的屋顶上长着一块块苔藓,绿得惹眼。
他在想,要是居住在农舍里的人知道恬静的生活就要被打破,他们会何去何从。
可是又转念一想,就算他们知道悲惨的命运正等在前方,日子与过去也没什么两样,只要有坚定的信仰,奇迹就会发生。他告诉自己,这也许正是要把他们消灭殆尽的原因。他来这里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死亡的时刻提前一些。等过了今天,他们将无力回天。骑手把边防士兵留在摩托车把上的指纹擦掉,继续上路。
离会面的地点越来越近了。摩托车怒吼着飞驰在人迹罕至的公路上,穿越山谷里缭绕的云雾。依稀还能记得的歌词从他的口中不经意间哼唱了出来。多亏这几句歌词,让他孤单的旅途暂时有了伴侣。车子在崎岖的乡村路上前行,四周一片空茫和沉寂,让他的心也变得空落落的。
最后,他到了目的地。这是一栋被遗弃了的农舍,屋顶像马背一样凹陷了下去。尊达普摩托车下了主路,穿过围在农家庭院周围的一道石墙。农舍被掩映在树林里,粗壮的树干上爬满了常春藤。一群奶牛悠闲地在院子里散步,地上的水坑倒映出它们庞大的身影。
骑手关掉引擎,四周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这让他有些不习惯。他脱下手套,挠了挠下巴。粘在下巴上的泥浆已经干了,很容易就能剥落,像除去结痂的疥癣,露出下面好几天都没有刮的胡楂来。农舍的窗户上搭着松松垮垮的百叶窗,叶片已经腐朽了。大门好像被人踢了一脚,平躺在房子的人口处。蒲公英在地板的裂缝中倔强地生长着。
他支起摩托车的脚架,掏出手枪,蹑手蹑脚地朝农舍走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