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君远在1957年5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纸应该这样干下去吗》一文中说:“去年秋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位同志到上海搜集教材,和我谈了一些有关新闻业务的问题。我把过去的经历讲了一些,又把当时我与新华社上海分社一-位记者会见的情形谈了谈。他们叫我把那次会见写成短文,送《新闻与出版》刊登。文章的题目是‘我受了一次审’。我的主要意图是想说明记者培养之难, 个记者要常识丰富,要熟悉业务,要具备采访风度。不久我就接到人民大学来信,说我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们预备——发表。”
可见,许君远在1956年秋以后,就开始在报刊上“鸣放”。次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全国开始“大鸣大放”。短短两三个月,许多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鸣放”,或发言,或受访,或写杂文,或者以其他活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百家争鸣”的气象一时在全国成为潮流。
这年的4月25日、5月21日,许君远分别在上海出版系统座谈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会议上公开表达表达了对新闻管制、不受重视等问题的不满。他说:
编辑人员都是调来的,不是考的。出版处调来,出版社领导没有权考虑没有时间考虑能不能用。就是考虑亦只是政治上的问题,对专业知识方面不了解…~上海出版通俗读物的“野草闲花”这对群众没有害处,亦是精神食粮,是人民需要的……编辑部与经理部有矛盾。多插了图,排得稀一点是浪费,《明清故事选》一书翻开来,上面是内容提要,下面是目录,行距那么密,多难看,这叫节约吗?……为什么我们这班有专业知识的出版工作者就应该不受社会重视,不受作家尊敬,也不蒙政府垂青呢?长此以往,势必造成人人视编辑为畏途,不敢问津尝试。其结果出版社徒存空名,出版物的质量将大受影响……有一些编辑同志还是硬搬教条,强调政治意义,一碰到男女关系就不敢大胆放手,对于一夫多妻的故事,总是设法删改,使之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对于谈情说爱的描写,更是畏之如蛇蝎,好像男女不应该恋爱,只凭领导安排就是。这对读者起什么教育作用呢?……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宗派主义倾向,倒是向作家开着大门,不像作协对我们大门禁闭。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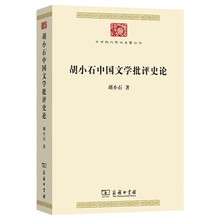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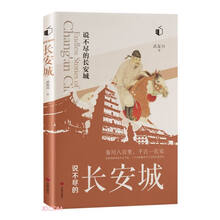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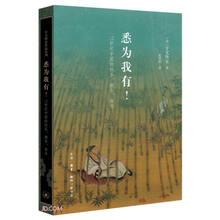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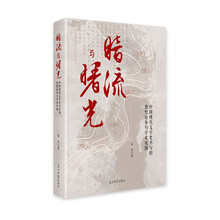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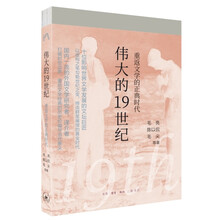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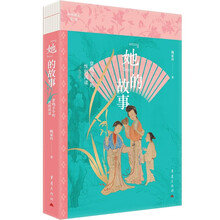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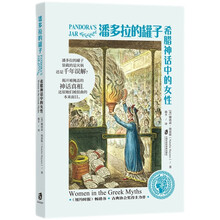
——汤一介 乐黛云
对梅杰(眉睫)十年学术文集的出版,我持十分欢迎和肯定的态度。梅君发掘和研究“失踪作家”,即近几十年来被冷落和忽视的作家之功,陈子善、谢泳等先生都作了很好的论述,珠玉在前,无须重复。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即是梅杰关心的首先是他本土和本姓的作家,这一点实在具有很不一般的意义。从低一点的视角看,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由切己而普世,此正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研究方法。从高一点的视角看,中国社会根本上就是乡土的和宗族的,近几十年变化虽多,本质却还依旧。梅杰用这种方法取得的成绩(包括挫折和失败),也就具有更为广大和深远的意义了。因此,我十分看重梅杰的工作,认为其指标性的价值,实在不亚于其学术文章达到的水平和创造的价值,也许还更大一些,更值得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关心也。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