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一、出发
日月山往事越千年
二、青海湖的黄昏
高原反应的折磨
三、校车上的学生
茶卡盐湖的科普
四、柯柯镇的清冷和诗意
唐古特人出没之地
五、奇遇
德令哈的错觉,不落的夕阳,买买提明的生意
六、穿越柴达木盆地,
两个穆斯林的“昏礼”和一个“塔琏湖”的美梦
七、穿越盐泽戈壁,
黑夜中的雅丹,老茫崖的南八仙
八、翻越阿尔金山,
在花土沟告别祁漫塔格
九、进入库姆塔格沙漠
古丝路南道的起点 楼兰古国,罗布泊、米兰遗址
十、走进塔里木盆地
瓦石峡,沙漠绿洲,车尔臣河边滑沙
十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
且末的维吾尔农庄,南疆的棉花与哈密瓜
十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民丰县,塔中油田,沙漠第一村与安迪尔古城传说
十三,浩渺茫茫的沙漠腹地
尼雅河,精绝古国
十四、分手,依依惜别
于田县的好运气,见到库尔班大叔
十五、闯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克里雅河尾闾,沙埋古城的传说,达里雅布依乡
十六、沙漠腹地的绿洲
达里雅布依乡的篝火晚宴,喀拉墩沙漠遗址
十七、告别达里雅布依衣乡
故事里的沙漠遗址丹丹乌里克,绿洲生态
十八、向昆仑山致敬
重返丝路南道,和田软玉,玉帛之路
十九、昆仑山下的南疆重镇
漫步和田市,古城寻踪
二十、今昔于阗古国
瞿萨旦那“地乳”的传说,疯狂的掘玉人
二十一、钻进玉龙喀什河大峡谷
喀什塔什乡,昆仑山脚的挖玉人,一伙土匪的故事
二十二、昆仑山脚的“黑山村” 喀拉古塔格
徒步的天堂,中国最原始美丽的村庄、电视民工库尔班江
二十三、和田的穆斯林绅士
佛教与伊斯兰教的于阗大撞击,以及和田美女
二十四、离开和田
喀喇汗王朝,历史的“口香糖”
二十五、喀喇汗王朝的崛起
抵临喀什噶尔之夜的百年宗教战争,真主伟大
二十六、南疆重镇喀什噶尔
语言障碍的烦恼,老乡,一段伟大的世纪对话
二十七、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古代东西方商贸之结,文明交汇之结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选择的宜居之地
二十八、阔孜其亚贝西
吐曼河边的高台民居,游走古巷
二十九、层层叠叠的民居,曲径通幽的街巷
庭院、老人和孩子,土陶作坊的吾术尔大妈
三十、 喀什噶尔巴扎
漫步古城,“原点在这里”
三十一、 艾提尕尔清真寺
《古兰经》说,“贫困会使人变得脆弱敏感,也容易使他被别人影响”。
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关于麻扎的一个寓言故事
三十二、 前往帕米尔高原
红山,穿过盖孜峡谷,翻越九别峰“山墙”
三十三、 葱岭,“世界顶上的第二层楼”
布伦口山谷下的白沙海,与公格尔峰握手
三十四、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
喀拉库勒湖,苏巴什达坂,萨雷阔勒岭
三十五、塔什库尔干塔吉克
石头城,在塔格敦巴什帕米尔谷地,柯尔克孜人毡房
三十六、终点,红其拉甫边防哨所
帕米尔高原雪山“结点”,古代丝绸之路冰川关隘,昆仑山颂
三十七、没有终点的结束
一条伟大的冰川古道,写在明铁盖达坂冰川的书信
后记
跋:回到“一个人的西域”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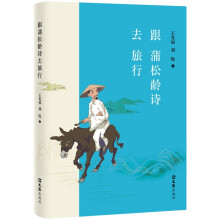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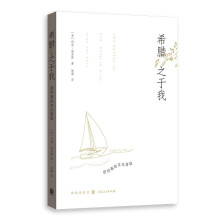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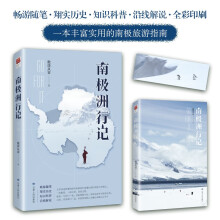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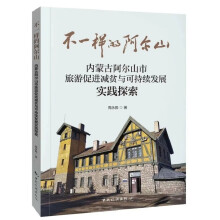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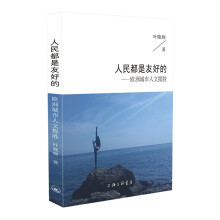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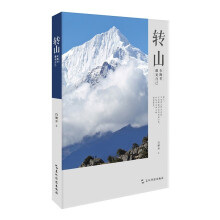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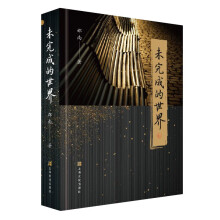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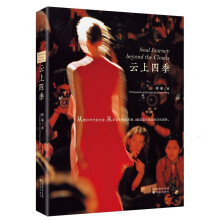
——汤因比(英国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