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丹东
中国到哪里去?谈到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喜欢拿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与之相提并论。比如说它像辛克莱尔《丛林》里的美国,像水俣病泛滥时期的日本,抑或更像政治和解之前的南非——那时候南非也有人会莫名其妙地死在监牢里,而原因据说是他在洗澡时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肥皂。
当然,读者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历史截面,说今天的中国像是某个时期的苏联、北非、阿富汗,甚至中东——理由也许只是前些天中国某个地方竟然也发生了自杀性袭击事件。如果遇到一个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他可能还会皱着眉头说现在的中国像先秦,像盛唐或者晚清。总之,只要你愿意,总能找到几个可以重叠的特征,将两个天遥地远甚至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时代联系在一起。但那些特征却又是真实的,绝非杜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关于大革命时期法国的评价似乎同样适于今天的“盛世中国”。这里是朝气蓬勃的新世界,又是悖论满身的旧王国。这里愚蠢与聪明交织,黑暗与光明缠绕。这里有的人踌躇满志,有的人垂头丧气;有的人富可敌国,有的人家徒四壁;有的人直登天堂,有的人直下地狱。
一
201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在西单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和一位法国学者聊天。他说,今天的中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欧,也像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我笑了笑,说如果对照法国历史,今日中国所处的时代既像法国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国大革命之前。理由如下:
前者,1789年开启的大革命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成功,革命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进步,同样带来了预料之外的恶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时代。革命不过是历史转型的开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许多法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已经惧怕流血,从而寄希望于日积月累的社会建设。我曾说中国是“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纪代替流血之世纪,也是今日绝大多数中国人之所想。
至于说像法国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说社会矛盾使中国一定会再次爆发革命,而是说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时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国面貌一新:政治由专制走向开明,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国民自由可谓有增无减,然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生活难以忍受。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就好比一个生来手脚都被戴上镣铐的人,当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铐,自由虽然增加了,但这种局部改善可能让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让他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当他开始行使双手的自由时,不仅发现脚上的镣铐会间接限制双手的自由,还有可能将脚上的镣铐视为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为此感到羞耻;其二,因为恢复了对现实的疼痛感,在手铐被去除后,他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脚镣同样应该去掉,道理是一样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个被绑着四肢的人,双手的自由将为他除去脚上的镣铐提供条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虽然他已经着手改革,但他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格局却没有跟上巴黎那些脚戴镣铐的“半自由人”冲向巴士底狱的速度。
谁也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从整体上说,今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之三十年前大有改观。然而,由于公权力尚未得到有效约束,社会间的侮辱与损害日积月累,再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权利观念的变化,这个“最好的时代”正积累着某种“最坏的时代”才有的革命情绪。
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李泽厚与刘再复一齐喊出“告别革命”时,他们的思考被认为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而在2011年底,当年轻的韩寒因为“不想再讨好任何人”而公开“拒绝革命”时,他却在一夜之间成为“叛徒”,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尤其是“革命派”的冷嘲热讽。无论你是否支持或信任韩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最初对“政治不正确”的讨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倒韩运动”,韩寒的“拒绝革命”是导火索。
二
法国如何终于告别革命——在十九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发生近百年之后?
法国大革命推翻旧制度,被视为历史的进步。然而革命的马车最终失控,冲进了人群。理性的冒险变成了现实的灾难。此后若干年里,法国更是在帝制与共和之间摇摆不定。有人说,麻将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来,可历史却从来不给人假设的机会。
盘点法国如何告别革命,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将功劳记在了第三共和国的国父们身上,正是他们给法兰西带来了一套和英美宪政民主类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两院议会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罗桑瓦龙则认为关键在于公民社会的成长。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后,法国的工会、政党、选举委员会、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为普遍的社团组织让法国社会渐渐脱胎换骨。
除此之外,知识阶层的痛定思痛同样功不可没。
大革命发生以后,远在英国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峡对岸暴躁的法国人不知道珍视本国的价值与传统,正在让法国变成“文明的废墟”。值得庆幸的是,法国没有走上“不断革命”的不归路。十九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从贡斯当到托克维尔,从圣西门到孔德,从雨果到左拉,法国的思想家、文学家为法国社会理性和心灵的重建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使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以及人道主义、法的精神等在血腥的革命之后得以续接。正是政治与社会的多线并进,使在革命浪潮里风雨飘摇的法国船绝处逢生,像傅勒所说的那样,“大革命驶入了港湾”。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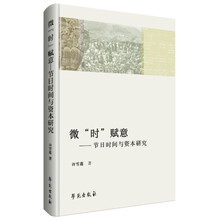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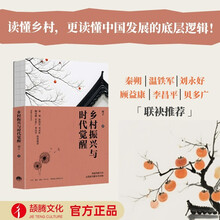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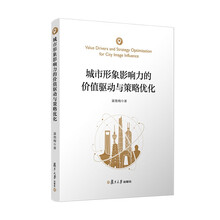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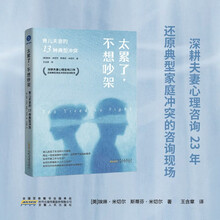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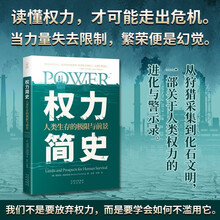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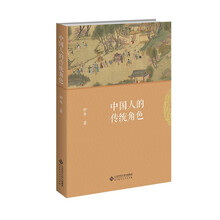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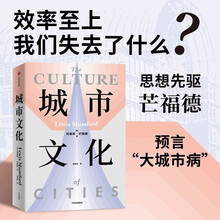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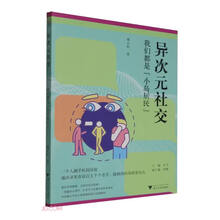
——京东用户评论
今年1月份的新书,根据近两年的讲座材料整理而成。分析事物相当入理。 熊培云的书一直温和理性。
——京东用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