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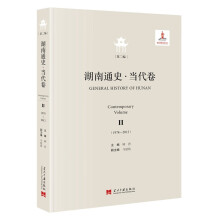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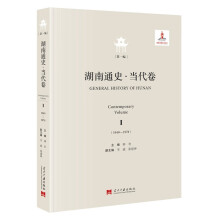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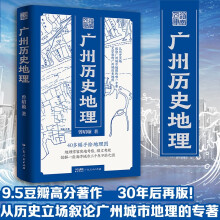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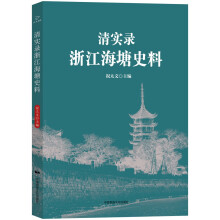

《澳门古今与艺文人物》分为甲乙两辑。甲辑“澳门古今”写澳门的历史背景和沧桑变化,对澳门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有所叙述。“澳门古今”从澳门开埠写起,每篇五六百字,篇篇独立而又前后连贯,把澳门的历史和地理知识都交织在一起,俨然一幅澳门的古今图景。乙辑“艺文人物”写与澳门有关的艺文人物,譬如秦牧、启功等。
来澳必游大三巴
来澳游客,不论是来自香港或是欧美各大洲的,很少不到大三巴牌坊去。
这个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建筑,恢宏高峻,造型雄奇,充满宗教色彩的艺术雕塑,着实是有其独特的风格与迷人的魅力。即在文物价值来说,也是澳门最古老的艺术性建筑之一。
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曾经在大三巴牌坊前作过《欢乐今宵》的直播演出。艺员们在牌坊前的平台载歌载舞,颇有点在古罗马剧场上演出的气氛,也能勾起观众发思古之幽情。
近年也有过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新婚夫妇,集体来澳度蜜月。数十对新人穿上礼服,披上头纱,在大三巴牌坊前拍集体照,这种风味在以后银婚、金婚的日子里,也是一个美丽的回忆。
今日我们所见的大三巴牌坊,其实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三”是Sao的译音,“巴”是Paulo的合并译音,所以称为大,是有别于当时另有的一座三巴仔教堂,这就是“大三巴”名称的来由。
圣保禄教堂历史悠久,在我国的古籍中称为“三巴寺”,《香山县志》、《澳门纪略》以及一些名人笔记,都有记述。这原是葡国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澳传教的一个基地。1565年,先在今址的小丘旁用木板土石,筑成栈仓型小室,以传教及供教士潜修之用。奠定雏形则是1580年起陆续兴建的修院及小教堂。不过这最早的建筑,已在1595年的一次大火中全部焚毁了。
三次火烧余前壁
大三巴牌坊,原是圣保禄教堂的前壁。
这个教堂可说是与火有缘。从其雏形起至今残存的前壁,中间经历了三次大火,屡焚屡建,终于仅剩现在可见的牌坊。
第一次失火在1595年,整座教堂和修院完全焚毁,连同图书典籍,亦难幸免。之后,耶稣会为传教需要,不久又照样建成一座小型教堂和修院。不料到1601年,又遭第二场火灾,烧剩修院的一个讲堂,权作教堂之用。
接着,耶稣会发动葡商筹款进行第三次重建工作,并由史宾诺拉神父设计,在1602年奠基,到1637年始将前门石壁,即今大三巴牌坊竣工,历时三十五年。
建筑时间拖得这么久,一方面是由于重建工程着重坚固精美,不能不费时间;另一方面却是尽管筹得款项不少,但在重建过程中仍感不敷,以致不得不随时募款逐步完成。
从今日的烬余建筑看,还可发现后者的痕迹。牌坊背后的屋顶砖痕,并非出于自然建筑的,乃是1637年彼得文地神父来澳巡视,始将教堂与壮丽的前门联接起来。
教堂前的石级,是在1640年新添上去的。我们现在很明显地看到它并非正对牌坊,而是倾侧一面。如果当年有个统一的完整规划,是绝对不会出现如此不协调的现象。
牌坊耗银三万两
大三巴牌坊巍峨壮观,雕刻精美,三百多年前的造价已达三万两银之巨。
整座圣保禄教堂的建筑,糅合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与东方建筑的风格而成,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建筑、文物、艺术界人士的重视。
今日游览大三巴牌坊,细心的旅客会看到其右方还有一个石围杆夹。其形制与中国过去的衙署或祠堂庙宇前所竖立的无异。按照封建皇朝的旧例,只有高官显宦的府第,才获准在门前竖立围杆。因为当年耶稣会的神父及圣保禄修院的毕业生,不少受到明清皇帝的册封,所以也享有这种炫耀勋禄的特权。时日久远,左右成对的石围杆夹至今已仅存其一。
建筑圣保禄教堂出力至大的应数日本教徒。17世纪初年,日本政府严禁奉教,天主教徒纷纷逃来澳门,聚居在三巴门一带。他们之中,不少是建筑工人和艺术工匠,耶稣会利用这些人才,以工代赈来建筑教堂,节省了不少经费,也保证了建筑质量。
不料建成使用还差两年就到二百年时,竟因为被葡军用作营房,修院的厨房储存大量柴薪,招来了第三次大火。1835年1月26日下午6时整,先由厨房堆柴薪处起火,时值隆冬,在东北风猛吹下,火乘风势,一发不可收拾。焚烧了两个多钟头,到8时15分,整座教堂付诸一炬,只剩下前门残阙供后人凭吊流连。
……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澳门众多的写作人,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
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
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
——摘自王蒙《澳门文学丛书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