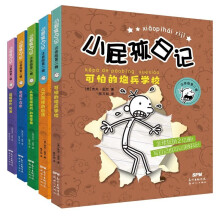二、血淋淋的惨剧
爸爸不见了,妈妈也不见了!我和哥哥呆呆地站在东屋门口,看着姐姐安静地睡着。
哥哥冲到院子里。月光如水,清冷、寂静,只有咚咚的声音时隐时现。那声音好像很压抑,怕惊扰了夜的宁静似的。咚!我侧着耳朵听,它仿佛来自天际,又好似发自脚下。“哥!”我低低地怯怯地唤着。
静默的院墙和远处的树都是黑色的。那些树在晚上看起来有些恐怖,好像树冠中藏着怪物,随时都会扑过来,吞噬我!哥哥将他粗壮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我的心情才变得平静一些。咚!又是一声响。我仰头看着哥哥。他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拉着我蹑手蹑脚朝东屋前面走去。东屋前面有个地窖,冬季用来储存白菜、红薯、萝卜等食物。难道有人来偷我们的东西?我的心怦怦跳着,大气也不敢出。
地窖上面罩的是荆条编的笸箩,以前都是扣着一口破锅。哥哥走到笸箩面前,慢慢蹲下身子。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在他身边蹲下。咚!这一声响吓了我一跳。这响声就是从脚下发出来的。“嘘!”哥哥示意我稳住情绪,不要出声。
我们听到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地窖里传出来,虽然很细微,但还是被我们捕捉到了。哥哥按了下我的肩膀,让我待在原地不动。他悄悄从墙根拿来铁锹,随后猛地掀开笸箩。地窖里有微光在闪烁,似乎有影子在晃动。我的心怦怦跳着,好像要冲破胸膛蹦出来。
谁在地窖里?他们在干什么?我瞅了一眼哥哥。哥哥紧绷着脸,鼻翼急促地翕动,却听不到他的呼吸声。我感到他握铁锹的手在发抖。我轻轻碰了碰他,他的目光如同钉子一般,钉在地窖里面。
东配房在月光中沉默着。爷爷住在那儿。他在吗?我瞅了一眼东配房,屋里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听不到。我的目光重新回到地窖上。地窖位于正房和东配房之间的空地上。
那黑黢黢的地窖里,忽明忽暗的光,摇曳扑朔的暗影,这些影像叠加起来,就像一只凶狠的利爪,伸向我。它要把我那颗紧张地撞击着胸膛的小心脏抓出来,撕得稀巴烂。我仿佛看到鲜血从地窖里洇出来!我的喉咙酸酸的,鼻腔也酸酸的。我想逃回屋里,整个身体钻到被窝里!
“谁?”地窖里发出一声质问。这声音是特意被压低的。“我!”哥哥瓮声瓮气地答。他握铁锹的胳膊抖了一下,做好攻击准备,好像有鬼子要从地窖里冲上来似的。我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铁锤!”这是爸爸的声音。爸爸的声音富有磁性,我听了很舒服。
“爸!”我不禁喊出声。
“回屋睡觉去!”爸爸低低地呵斥道。
“你在干什么?我妈呢?”哥哥问。
“让小乐回屋睡觉,你下来帮我们!”爸爸没有回答哥哥的问话,而是像校长一样给我们下了指令。我也想下到地窖里看个究竟,可是却被哥哥强行推进屋,强行按进被窝。
听着哥哥走出屋子的脚步声,我心有不甘。同样都是男孩子,爸爸为什么不让我进入地窖?他们在下面干什么?妈妈呢?我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爸爸说让哥哥下去帮“我们”,难道妈妈也在地窖里面?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努力思考着这个问题。没等我想出答案,眼皮就开始不争气地打架。咚咚的声音又响起来,我在月光的抚摸下慢慢进入混沌状态。第二天,我一再刨根问底,哥哥才告诉我,他和爸爸、妈妈偷偷挖了半夜地窖。爸爸说,把我家的地窖挖深挖大了,万一鬼子再来扫荡,我们可以藏到地窖里。为了我们上下方便,爸爸还在地窖的壁上掏了几个坑。我们可以脚踩着坑、手扒着坑下到地窖里。
天气越来越暖和,大田里的小麦开始返青,地里的草也偷偷冒出嫩芽。要是往年的这个时节,我和王小奎早到麦田里放风筝了。可是今年不行,那些脚蹬皮靴、身着草绿色军装的鬼子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据爸爸说,前些天一个在街上玩耍的小孩,被一个进村找粮食吃的日本兵用刺刀穿透了胸膛,还被举到半空中示众。那血顺着刺刀流下来,溅了日本兵满手。他这才边狞笑着边呜里哇啦叫喊着将那个孩子摔到地上。我可不想被那闪着寒光的刺刀挑到半空中!学校里的课松弛下来。张校长——也就是我爸爸经常和老师们开小会,好像在密谋什么。我们这些孩子自然把课堂吵翻了天。嘘!如果有鬼子靠近学校,我们断不会这样大声的。
你也许会问,我们是怎么知道鬼子是不是在学校附近的?实话说,我们学校加强了“武装”防备,成立了教师护卫队和儿童团。上课的时候,由没课的教师组成教师护卫队轮流站岗;课间的时候,由儿童团的孩子们轮流站岗。
……另外,在爸爸的大力推崇下,我们学校也挖了好几个地洞,专门用来防备鬼子突袭。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大树们纷纷长出嫩芽,村口的老槐树分外茂盛,鹅黄的新叶彰显着它旺盛的生命力。老槐树是我们冉庄的吉祥树。据爷爷说,这棵树是唐朝栽种的。唐朝,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一棵槐树能活那么多年吗?我怀疑它的身世。不过,怀疑并未影响我对它的好感,因为老槐树给我带来许多快乐!不说那白玉似的槐花可以当美味,也不说槐花开得正旺时飘得满街都是花香,那是女孩子喜欢描摹的事情。单说槐树那巨大的树干,我们男孩子喜欢在它上面捉迷藏,玩骑马打仗,喜欢到它上面掏鸟窝,寻鸟蛋。简单地说,老槐树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远远多于其他的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姐姐从村口的野地边挖来一棵狗尾巴花,种在距离地窖一米多远的地方。我嘲讽地对她说:“你还真把狗尾巴花当成红蓼了?那是爸爸安慰你的话!”姐姐朝我扬了一把土,我嬉笑着躲开。不管我怎样嘲讽姐姐是狗尾巴花,姐姐都不再恼我,因为她的心思转移到那棵真正的狗尾巴花上。我想,她一定盼着它开出世界上最美的花来,那样,她就可以证明给我看:狗尾巴花就是红蓼!为了防备我破坏那株花,姐姐在它周围插了一圈小树枝,权当篱笆。呵呵,我可能去践踏一株花吗?况且是田边、地头、河滩常见的狗尾巴花!简直太小瞧我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