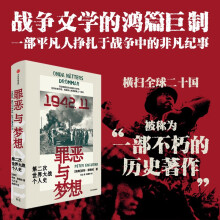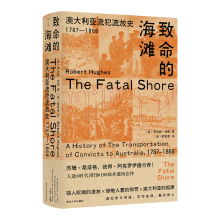那一晚我并没有回去,森林里面我听到右翼六十四团的机关枪和手榴弹越响越近,快要和我们并头,部队长因为雨声可使行动秘密,又加派了第一营另辟新路到敌后去。这都是很好的消息,我想再待一夜。黄昏之前我打电话给郑参谋,叫他不用派车来接我。
相处两日,我和营长以下树立了很好的感情。我才知道我们的军官都是面红红的像刚从中学校出来的男孩,但是事实上他们比敌人留着半撇小胡须好像都是兵学权威的家伙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看到这些干部早上挤出牙膏悠闲的刷着牙齿,或者从背囊里拔出保安刀修面,我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把战斗当作了不得的工作,仅仅只是生活的另一面。
起先,我总奇怪,这些弟兄们作战这么久,怎么一身这么洁净?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任务稍微清闲或者调作预备队的时候,就抽出时间洗衣,一路晾在树枝上,随着攻击前进,至晒干为止。有时候看到他们吃过早饭就将漱口杯紧紧的塞一杯饭准备不时充饥。有些弟兄皮鞋短了一只,一脚穿上皮鞋,一脚穿上胶鞋,令人触发无限的幽默感,也令人深寄无限的同情。部队里的工兵和通信兵,技术上要求他们紧张的时候松弛,松弛的时候紧张,而他们也就能够做到那么合乎要求。……
一位弟兄分给我一包饼干,我知道他们自己的饼干都不够,但是他们一定要塞在我的手里:“这是上面发下来,你应该分到这一包!”
另一位弟兄帮我培好掩蔽部的积土,然后笑着说:“保险得很!”
那一晚我有我“自己的”掩蔽部,窦的两个传令兵找了很多迫击炮弹筒,替我垫在地面,筒上有一层桐油,我再不感到潮湿,我把背囊里的橡皮布和军毯,学着他们一样,好像在钢丝床上慢慢地铺得很平,再不想到背水阵和梯次射,很安稳地在枪炮声里睡着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