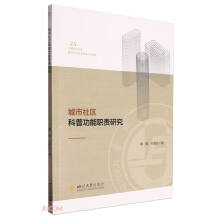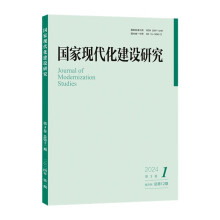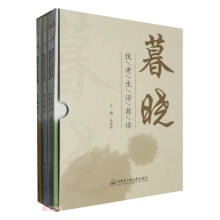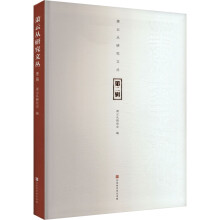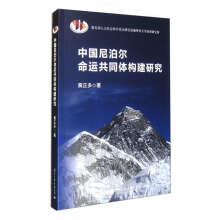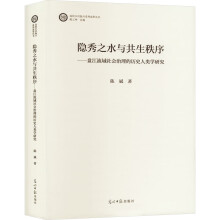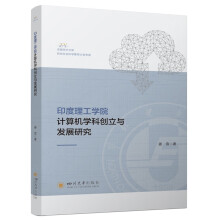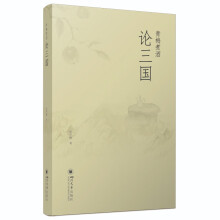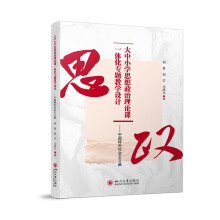《新知文库:疯狂实验史(2)》:
他曾做过一项令人不安的实验:实验参与者是一群女性,她们都戴着一副面具,穿着一条超大围裙,谁也认不出谁,她们要对另一个人进行电击。在伪装的情况下,她们施加电击的持续时间与没有伪装并且佩戴姓名标牌时相比,整整翻了一番。这一效应被称为“去个体化”,它会导致身处群组中的人做出他们作为个体绝对不会做的事情来。
不过,上述实验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弗雷泽想要知道,这一效应在实验室之外,也就是在自然环境中是否也能得到证明。于是他打起了万圣节的主意:11月1日前夜的“变装”传统对他的去个体化实验十分有利。于是他开始寻找研究助手,以及愿意送孩子们来参加聚会的家长。
尽管弗雷泽对结果早有预料,实验的进展还是让他吃了一惊。在所有人都穿上变装服饰之后,一种攻击性的氛围迅速扩散开来。这时再让孩子们去参加比赛,更多的孩子就会选择对抗性的游戏。许多人甚至干脆不玩游戏了,而是互相推撞、大喊大叫或者彼此殴打。
那盏黄色的灯仍然每隔20秒钟闪烁一次。随着这一节奏,各位研究助手会观察并记录,此时哪些孩子的表现具有攻击性。弗雷泽希望通过比较各组数据,研究由变装带来的匿名化效应是否推动了群组中攻击性的增长。孩子们不再老老实实地投掷水球,还会拿平衡游戏里使用的木板作为武器来进攻,混乱的局面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难度。
与实名阶段一样,匿名阶段本来也该持续一个小时。“然而情况完全失控了,”弗雷泽说,“我已经不太担心孩子们的安全,而是担心起研究助手们的安全来。”因此他提前中止了这一部分的实验。
他编了一个借口,说另外一个聚会还要使用这些变装服饰,孩子们必须把它们脱掉。之后他们还能再玩1个小时,依然可以赢得兑换券。没有了变装服饰的孩子们立刻又平静下来。通过统计兑换券的数量可以看出,攻击性的行为对他们有害无益:在变装阶段,每个孩子平均收集到31张券,而在之前的阶段是58张,在之后的阶段甚至有79张。群组中的匿名性促进了攻击性,尽管从根本上讲,这与个体的利益相悖——兑换券数量下降就是一个明证。“攻击行为带来了‘游戏的乐趣’,这就是它本身的奖励。在这一奖励面前,其他更加遥远的目标则被忽略了。”菲利普,津巴多日后写道。
后来,斯科特,弗雷泽从纽约来到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再一次为万圣节实验寻找起了“受害者”。与在纽约的实验不同,这次实验并非只在一所房子里,而是在西雅图的27所房子里同时进行。通过预谈,他获得了这些房子的支配权。所有房子的入口处看起来都一样:一张桌子上放着2只碗,一只碗里装着糖果,60厘米之外的另一只碗里则装着零钱。按照传统习惯,住在附近的孩子们会挨家挨户敲门讨糖。一位他们并不认识的女士会把他们请进门,并对他们说:“每个人都可以拿1块糖。我得回另一个房间干活去了。”
现在孩子们被单独留下,自由行动:有些孩子很听话,只拿了1块糖,另外一些则拿了2块,或者向放着零钱的碗里抓去。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弗雷泽的一位助手正藏在柜子里,通过一个微小的窥视孑L观察着他们。
这次实验再次证明了群组中的匿名性所带来的影响:如果那位女士在离开房间之前询问过孩子们的名字,只有21%的孩子会去偷窃。如果孩子们保持匿名,比率就变成了57%。另外,那位女士有时会对群组中的一个孩子单独强调:“如果丢了什么东西的话,就是你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有80%的孩子会去偷窃。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