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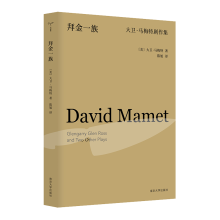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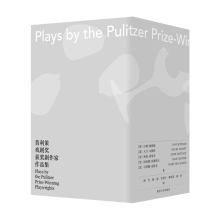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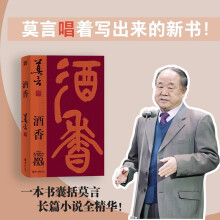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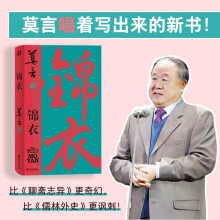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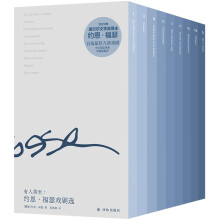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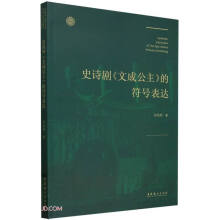
《昆曲大观》计六卷二百四十万字,真是洋洋大观的煌煌巨著。内中对精彩纷呈的昆曲世界有极为生动活泼的描绘,特别是写人记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中国昆剧大辞典》主编、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新雷
《昆曲大观》是一项为昆曲人立心、为中国百戏之师溯源、为世界文化遗产代表作招魂的宏大工程。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柏梁
《昆曲大观》把我们这一辈昆曲人,特别是我们老师的人品和艺品记录下来了。作者一边采访,一边就有人过世。实际上作者是用自己的精神“抢救”了历史。而这个历史全都是健在的昆曲人的“口述”,他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
《昆曲大观·名家访谈:上海 香港 台湾》 为上海、香港、台湾昆曲名家访谈录,采访对象涵盖蔡正仁、岳美缇 、华文漪 、梁谷音、张洵澎、王芝泉、计镇华、郑培凯、王安祈、张静娴等近三十位昆曲名家、曲家、学者, 其中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昆曲艺术家,按照生旦净末丑的顺序排列,采访内容涉及访谈者从艺经历、对昆曲的感想、昆曲的前尘往事,该书口述历史,如同昆曲活化石。
上海
朝飞暮卷
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
烟波画船
生
蔡正仁
1941年7月2日出生,江苏吴江人。工小生,尤善大官生,有“小俞振飞”之美誉。师承俞振飞、沈传芷等昆曲名家,同时得到姜妙香、周传瑛等指点。音色宽厚洪亮,表演洒脱大方,唱念俱佳。代表剧目有 《 撞钟 》 《 分宫 》 《 惊变 》 《 埋玉 》 《 迎像 》 《 哭像 》 《 太白醉写 》 《 见娘 》 《 乔醋 》 《 评雪辨踪 》 等。国家一级演员、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传承人,曾担任上海昆剧团团长十八年。
时间:2013年7月27日
地点:苏州朴园
陪访:钱瑜婷、卫立、依兰
杨:2011年7月,纪念俞老诞辰一百零九周年的活动,会上说到,有人曾污蔑俞老,大家非常气愤。是不是可以从这里说起?
蔡:对俞老的攻击,主要是说什么俞老唱京剧,不像“传”字辈老师一直坚持。其实“传”字辈老师当时为生活所逼,纷纷改行,虽然没唱京剧,但是跟苏剧在一块儿唱苏剧去了。有些是干别的。我觉得都是无可非议。人家活都活不下去,你也不让人家找口饭吃?
在昆曲最最困难的时候,我就没有看到这些人站出来,为昆曲作一点贡献!现在大家开始重视起来了,你就是昆曲卫道士,好像保卫昆曲一样。真的,我是很看不起这种人!然后他又觉得某某某谁谁谁当时昆曲不唱,他去唱京剧。好像是在为昆曲鸣不平,他忘了一条,昆曲到这种地步是谁造成的?不是这些昆曲艺人造成的,是当时社会造成的,是当时社会制度造成的。你去埋怨这些艺人,我觉得毫无道理。
以周传瑛、王传淞他们为代表的这些人,跟朱国梁一起——我非常钦佩朱国梁,他不仅把这些昆曲艺人、“传”字辈老师吸收到他的国风苏剧团,让他们有一碗饭吃,而且我觉得他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让苏剧向昆曲学习。在苏剧里头唱了很多昆曲,也掺杂了演出昆曲,甚至于他带头演昆曲。 《 十五贯 》 是最典型的,他演过于执。他是苏剧的顶尖人物,但是他带头唱昆曲,所以给昆曲的“传”字辈老师一席之地,这个我觉得是很了不起!当时周传瑛老师、王传淞老师,还有周传铮、包传铎这些人,“传”字辈老师为了生活能够在苏剧团坚持下来演演昆曲,有时候呢也要演演苏剧,真的是无可非议!
这个跟俞老师一样的道理啊。他单独演昆曲他也不行啊,维持不下去啊,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去拜京剧老师程继先下海,既演京剧也演昆曲。跟四大名旦在一块儿,也经常演昆曲,这个也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对昆曲所负有的责任和贡献。好多人拿这段历史老攻击俞老师,这是毫无道理的!一点道理都没有!!
事实上呢,俞老师跟程砚秋搞的 《 春闺梦 》,很多是昆曲的东西,对京剧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保留昆曲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能把它分开来说。
事实也是证明,由于他们当时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俞振飞学京剧、唱京剧,“传”字辈老师跟苏剧的一块儿,然后又到各个剧种去教戏、教身段,这个都是他们为了保存昆曲而采取的一种迂回战术。因为你要坚持不下去你人也活不下去,你还有什么保存下去的,不可能了!有些人是打着这种旗号,以所谓维护昆曲的这种面貌出现,来攻击俞老师,我觉得是毫无道理的!!
杨:真正的目的可能不在这里。
蔡:他的目的当然就是维护他们的小圈子。那个小圈子呢,对昆曲也稍微地接触了一点。说句老实话,他要跟“传”字辈老师比,跟俞振飞老师比,他谈不上,根本谈不上!他有什么资格来指责这些老先生,对不对?!对这种人我是很藐视的!!“传”字辈老师、俞老师他们这些人,在保存昆曲力量、维持昆曲发展这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宣传昆曲、教昆曲,拼命地以他们的努力来维持昆曲的生存。这个事情本身,比那些人动动嘴巴强百倍千倍!!
杨:主要的是想请老师讲,俞振飞作为你的老师,他的人品和艺品,你所感觉到的、直接体会到的一些东西。
蔡:俞老的人品艺品很值得我们这些人好好地努力地去学的。其实我跟俞老师学戏,也无时无刻不在学习俞老的为人。因为我觉得演员这个为人,跟他的艺术是决然分不开的!很难想象一个演员平时的格调低下,修养非常糟糕,没什么文化,这样的人在台上演柳梦梅、演潘必正、演唐明皇、演蔡伯喈,演得非常好。我简直难以想象!!
从这个角度来讲,俞老师的贡献,他对京剧小生的贡献就是,他在京剧小生当中他的书卷气给京剧小生树起了一块响亮鲜明的榜样!当然俞老的书卷气首先表现在昆曲上。比如他演的潘必正、柳梦梅啊,演的李太白啊,这些文人雅士都是书卷气十足,台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文人。
杨:我看的你的那本书里,学 《 太白醉写 》 讲了很多,很精彩。
蔡:是,因为我有亲身体会。老师他讲:他当时二十岁左右,跟沈传芷老师的父亲沈月泉学 《 太白醉写 》。昆曲当中原来不叫 《 太白醉写 》,是叫《 吟诗脱靴 》。后来俞老把它改成 《 太白醉写 》。老师说当时他学了 《 吟诗脱靴 》 以后,他就感觉到他演不好,不敢演。他觉得他二十岁不具备像李太白这样高深的文化修养和气魄,要想演好这个 《 太白醉写 》太难了。于是他就默默地把它藏起来,会是会了,但他不演。一直到四十出头,四十一二岁以后他才敢试演。所以他演的 《 太白醉写 》 是四十岁以后演的。
当时我是很想学这个戏,听这么一讲,我就不敢提了。但老师讲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让蔡正仁这些学生你们免开尊口,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明这个戏的难度。
那个时候我最早学的时候十八岁,我进学校四年,学了四年,根本就想都不敢想我要跟老师提出来学这个戏,根本不敢!为什么当时会提呢?是学校的领导,几次三番把我找去。他们当时搞了一个什么运动,就是“攻尖端、攻难关”,敢于向最困难的进行挑战,还有什么二十年赶上英国啊,反正就那段历史。
杨:1958年,“大跃进”那个时候。
蔡:是的是的。那个时候俞振飞是我们校长,但实际负责校里工作的是周玑璋。周玑璋就说:“蔡正仁,你敢不敢提出来‘赶超俞振飞’这个口号?”我坐在下面,听说要赶超俞振飞,我一下就吓傻掉了。我才十八岁,学了四年的昆曲,还没有毕业,要我来赶超俞振飞,从前叫捏鼻子做梦——异想天开,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但当时学校就是这么提出的。不仅提出来,还把我找到办公室,还问我敢不敢,我说超是绝对不敢,赶是可以努力去赶的,能不能赶上就……我心里想着我就不好说了。
“你有这个决心就很好,你就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不仅要赶还要超!”当时就是这么提的口号,然后呢,班主任还轮流找我谈,并提出来:“蔡正仁,你敢不敢把俞振飞的最拿手的 《 太白醉写 》 学下来?!”我一听就一下蒙了,听完以后我始终就没有任何行动。谁敢?后来领导又让我们要敢想敢做,实际上是逼着我去学。
当时我脑子里在想,别的没什么,但逼着我去跟俞老师谈想学这个戏呢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我想老师真能够答应我学,这是好事儿。于是我就跑到老师办公室外面,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是不敢开口。后来硬着头皮找老师。“你找我什么事?”“班里头找我谈话,要搞‘攻尖端’。”“好啊。”“问我敢不敢向俞老师学 《 太白醉写 》,我很害怕学不好,我要不提出来……”我吞吞吐吐的,我就等待老师的意思,我以为他一定是会说现在不要太着急,并缓和地来安慰我说,这个戏呢很难学,先学别的戏,总之我想老师不会马上教我。
没想到老师说,要学 《 太白醉写 》 这是个好事情,但是这个戏确实难。他说这样,我这个戏呢是跟沈传芷老师的父亲学的,我跟你沈老师是一个师父教的,我建议你先跟沈老师说,是不是请沈老师先教,把身段啊什么的教完了以后你再来给我看,我再把我演出的一些体会教给你。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两个老师,一个沈传芷老师、一个俞振飞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说明沈传芷老师是个大好人、好老师。为什么呢?我是先找了俞老,俞老让我再去找沈老师,并不是我先找了沈老师。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沈老师一听,他心里就要想啦,你先去找俞振飞不找我,然后俞老让你来找我,你就来找我了,就来跟我学了。我当然也有点顾虑,所以我找沈老师也是吞吞吐吐的,就怕沈老师不高兴。但是我真没想到,沈老师倒挺高兴,没这个那个。我说老师你能不能教我?他说,好啊,你明天就来学!很爽快,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
这样一来呢,我的 《 醉写 》 学了不到两个礼拜,老师天天教我,就把这个戏学了下来。我再跑到俞老那儿一遍一遍给他看。我这个 《 太白醉写 》 就是这样子学会的。
学校听说老师已经教了,领导很开心,马上给我响排,就在学校实验剧场开始演出。那时候我十八岁,现在回想一下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不懂啊。虽然说俞老二十岁学,到四十多岁才敢演,我心里想,没什么呀,我也学会了呀,老师二十岁我十八岁,我比他还年轻两岁。学了以后领导说好,明天就演。我居然也会很得意,演!那天晚上很多报纸记者都来看,肯定是学校请他们来的。俞老师跟沈老师都坐在下面看。第二天上海发行最大的 《 新民晚报 》,登了一大篇文章。
杨:那时的演出恐怕还是依葫芦画瓢。
蔡:对!演得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绝对不怎么样,但是没错就行了。当时演完了老师都到后头来看我,我说老师您说说对不对?两个老师都对着我就笑笑。俞老师最客气的,蛮好蛮好。现在想呢,蛮好蛮好其实是一大堆话呢,他就没说。沈老师更有意思了,更不多说话,可以还可以。我最怕沈老师说一句“蔡正仁,你还不是桩事情呢”,这句话就厉害了!沈老师他不大会骂脏话,骂人他不会的。他要是骂人的话那简直是不得了了,他最厉害的就是“不是桩事情”,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的,明白吗?你啊你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你上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个评语很厉害。他有时候也会说“你还差得远呢”,这句话比“不是桩事情”要轻。尽管“你还差得远呢”但总是还像点样子。“你还不是桩事情”根本就不像样。我们跟沈老师学了这么多年,都知道他的脾气。所以两个老师并没有彻底否定我,但是也没有夸我。这种“蛮好蛮好”是很勉强的,或者说存心是安慰安慰。
学校作为一个“攻尖端”典型,蔡正仁居然把这个尖端攻下来了。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不懂,我还真的以为俞老师还不敢演,我十八岁能够演我还不容易啊!还有点小小的得意。这样一来,一晃就十多年过去了,直到后来1964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还演过一次。总之演了不少,反正我们同学自己演,当然无法跟老师相提并论,但我们学生公演的时候我还是常常演,演到1964年。我还记得1964年的夏天是叶剑英同志要看,我还给他演过 《 太白醉写 》。
1964年的夏天演完以后再也没演过。为什么呢,因为从1964年大演革命现代戏开始,传统戏就不能演了,再到1965年就更不能演了,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就更糟糕了。所以一停就停到1978年上海昆剧团成立。
1979年,上海昆剧团第一次离开上海到南京进行巡回演出。当时阵容很强大,号称“七梁八柱”。我除了其他演出,专门贴了一出 《 太白醉写 》。在南京人民剧场演,当时南京最好的剧场就是这个人民剧场。我大概十多年没演过这个 《 太白醉写 》。演下来以后,我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不是我演砸了,也不是我演不好,而是我自己不满意,那个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就忽然感觉到,这个眼神啊各方面总觉得不舒服,总而言之我是不满意自己的演出,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到半夜睡不着我干脆就站起来开了灯提笔写信,给俞老师,这封信是这么来的。
我说老师, 《 太白醉写 》 自从跟您学了以后,“文革”中我中断了十多年,这次在南京我又演。我以为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当时也已经过了四十,我想应该是越演越好,可是我忽然感觉到,越演越觉得自己不够好、很不好,越来越不满意自己在台上的表现,浑身难过。我说老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
很快俞老师就给我回信,那个时候南京到上海,今天发出大概明天就能收到。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厚的信,赶紧扯开一看,我现在还记得,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的来信我收到了,他说我终于等到了你的这封信!
我一愣,我说我没跟老师说过要写,他说我终于等到了这封信,你终于说出了我几十年想要你说出的话,“我真的越来越体会到,为什么您二十岁学了这个戏一直到四十岁才演,我才明白。我本来不觉得,但是现在真的觉得这个戏确实是难。而且我完全理解老师为什么您要到四十多岁才敢演。我现在体会了。那天我演出完浑身难受,一举手一投足,都不太满意。”
他就说了,“你现在都不满意自己,感觉到这个不灵那个不灵,我看到你写这样的一封信,我感到非常高兴。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你是真的懂得了,有进步了。我们俗话说,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你就寸步难行。这个你懂了,开始有进步了。你现在感觉到 《 太白醉写 》 难演了,你觉得浑身不好受了,恰恰说明你有进步了。如果你还是自以为我很好,你就根本看不到自己不足的地方,把那些缺点都看成了优点,你蔡正仁就不可能进步。”
他就给我回了这封信,很深刻。不知道为什么,这封信我应该保存下来,但是因为巡回演出吧,就遗失了,这封信要是现在拿来看了,很好!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终于等到了”。
杨:他还是很注意方法,让你自己慢慢地去体会。
蔡:他一直很客气的,但是他说得很深刻。信我是找不到了,但是话我是记得。我是永远不会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俞振飞老师他在教我们戏的时候,一直很注意如何教我们怎么学习,怎么演戏,还有怎么做人。
他一直跟我说,我俞振飞长期以来的几十年,我一直是给人家配戏做配角的 ( 那个时候他演昆曲演得很少,他唱京剧去了,京剧当然是以配戏为主。要是唱昆曲,昆曲小生他当然是主戏,梅兰芳、程砚秋都是配戏 ),他说我就是配戏长大的。在舞台上壮大,他就是配戏配大的。
那个时候很多人重视主角不重视配角,有的人为了演配角而闹情绪,想不通。俞老知道了这个事儿,有一次在大会上,他就讲了“我就是演了一辈子的配戏,我照样是俞振飞嘛”,这是俞老讲的。“为什么不要演配角戏,我就是演配角长大的。”这个我印象太深了。听说我们有些人不愿意演配角,他很生气。
还有一个事情,我听老师讲的,包括老师的自传里也讲了这个事儿,我非常感动。就是梅兰芳在抗战胜利以后,他不是八年不唱戏了嘛,胡子剃掉以后,庆祝抗战胜利。那个时候梅兰芳在上海,上海的观众就盼望着要梅兰芳上台演出。梅兰芳当然也总不能不演戏,他就请了把胡琴吊嗓子。一吊嗓子,不行,京剧的高度他拔不上去。八年不唱了,梅先生很着急。这个嗓子一时半刻怎么来唱呢?
上海
生
蔡正仁 4
岳美缇 26
旦
华文漪 46
梁谷音 64
张洵澎 76
王芝泉 90
净
方洋 114
陈治平 130
末
计镇华 148
陆永昌 160
丑
刘异龙 192
张铭荣 213
附
周志刚、朱晓瑜 232
张静娴 252
叶长海 257
徐希博 277
倪大乾、冯力英 292
香港
郑培凯 322
台湾
曾永义 336
洪惟助 343
王安祈 357
蔡孟珍、杨振良 392
朱惠良 401
名家短评 408
后记 414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