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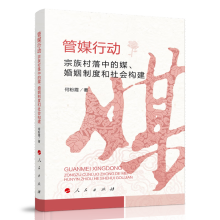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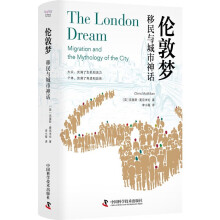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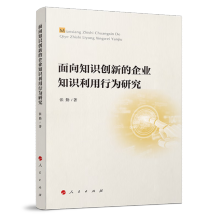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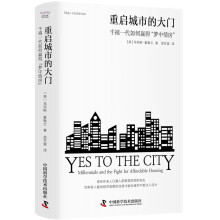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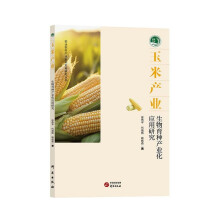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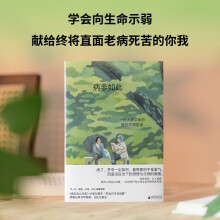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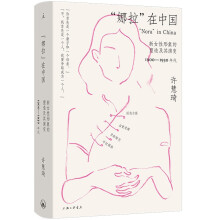


本长篇纪实文本以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视角作切入点,以编年史方式为经线、以心理历程为纬线,真实而细腻地描述了上海工人新村中工人子弟的成长过程,反映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叙事记忆是从上海的标志性建筑——旧上海时代经典建筑石库门和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初,那是“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的年代,开始了一家人跟随着在厂里做工人的父亲从常德路石库门房子搬迁到了控江新村的故事,由此开启了工人子弟生涯,也产生了石库门文化与工人新村文化的碰撞。
序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管新生兄属牛,生于1949 年,长我五岁。他坐在劳动榻车上被父亲拉着、举家搬进杨浦工人新村时,我才呱呱坠地数月。我们虽然算是同时代人,但这五年的差别非同小可。从学历上说,他属于“老三届”的1966届初中生,而我是1969届初中生,受教育的程度不可比肩。从人生经历上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在读初三,准备考高中;而我才小学毕业,连初中也没有读,就懵懵懂懂地进入了社会。所以,作为“老三届”的他,对上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历史有切身的感性认识,而我,多半是从家长们的窃窃私语中获得的间接材料。但是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近的生活经验:我也是在四五岁时,从黄浦区热闹地带搬到虹口区广中新村居住,开始了视野开阔而且生态丰富的新村生活;我们的中学生时期都是在杨浦区度过,他在双阳中学,我在靖南中学,我们走过同一条柏油马路;双阳路上的杨浦公园,是我与家人经常游览的场所,靖宇南路附近的控江文化馆,新生兄也一定在那里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这个工人生活区的文化环境对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成长都有过重要的滋养。因此,我读新生兄写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亲切和缠绵。
……
第一章 跨界行动·工人新村
1
上海的城市地标是什么?据史料云,代表上海开埠至今的建筑文化可历史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诞生的以石库门为代表的经典建筑,另一类是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这两种文化范畴,分别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记忆。
而我,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运之手轻轻一个拨弄,便实现了“跨界”行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带领着我们,举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杨浦区的控江新村,一下子从石库门迈入了工人新村。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必定连只言片语的发言权也无。
那年,我实足五岁,属于小赤佬一个,用北方话说,就是小屁孩。据一本已经发黄、发脆、老掉牙了的户口簿记载,那是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
至今在我记忆影像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长长的镜头:父亲埋头弓腰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平板人力车,是当年很常见的运输工具)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着,车上坐着奶奶、妈妈和我,妈妈怀里还抱着我一岁多的弟弟。在我的身边好像还胡乱堆放着几根长竹竿和几块木铺板。那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家具,我们是穷得只剩“清汤寡水”的无产阶级,就这样潦潦草草地开始了后来在记忆中那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乔迁之喜。
……
这样的长途跋涉、拖家带口,他们不但不知疲倦,反而是一路欢快。童年时的我,又如何能理解大人们的心事?直到近几年创作长篇小说,翻阅史料,方才恍然。原来在那年头,能住进工人新村,绝对是一大快事,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自是从历史的故纸堆中一不小心泄露了时代的心事:“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不少劳模可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住进工人新村的。那个时代的浪潮改变了我的一家,也影响了千千万万上海家庭的命运。
尤为令人叹服的是,当时的新村连选址都是大有讲究、颇具考量的。普陀的曹杨新村毗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分别紧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理工大学(原沪江大学,那时为机械学院)。政府的良苦用心十分显然,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
……
第二章 野蛮小鬼·瞎白相
1
记得初到工人新村时,我遇上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便是每隔一段时间,在睡梦中常常会听到一种一阵紧似一阵的莫名声响,更可怕的是,连床铺偶尔也会像筛子似的颤抖起来。伴随着这些的,还有闪电般的光亮一闪即逝,如同划亮夜空一般划破我的梦境。
梦耶?非梦耶?
谁也说不清。因为我压根不敢和大人们叙说。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那不是梦。
有一天,父母忽然忙开了,将所有的窗户玻璃统统贴上了呈米字状的防玻璃破碎的长条牛皮纸。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为了防范空袭。谜底就此揭破:那时台湾的飞机经常借着夜色掩护肆无忌惮地光顾上海的天空,欺侮大陆东海沿岸防空力量薄弱,这就引起了地面上的高射炮齐鸣、探照灯齐亮,并一不小心便闯入了我似梦非梦的“领空”中来了。听父亲说,隆昌路那儿驻扎着当时苏联老大哥的防空炮兵部队。
也难怪高射炮声没能把我惊醒,其实我们这些小孩每天都玩得很吃力、很疲乏。那时候的平民百姓家长们没有超前意识,比如让子女去学学琴棋书画,或者上上学龄前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各类补习班,他们对此没有一点儿觉悟。当然,也不可以完全责怪他们,而是那个时代还没觉醒。现在想来,他们倒是慷慨大方地将这些力气活儿历史性地搁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至今让我们又“孝子”又“贤孙”地负重前进,压得背也驼了、腰也弯了。像我们光景的这一拨人,那童年时代活得真的是既轻松又潇洒,白天是一晌贪玩,夜晚是一晌贪睡,打雷不醒,闪电不惊———径自沉浸在睡梦里,“幸福指数倍儿高”。
……
第五章 抓特务·资本主义尾巴
1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流行色。譬如,如今的追星一族被唤作“粉丝”,动辄人数以千万计,因为当下已踏进了网络社会。我们小时候也有自己的明星偶像,如赵丹、金山、金焰、孙道临、刘琼、周璇、上官云珠、秦怡、张瑞芳、白杨、王丹凤、王心刚、王晓棠、浦克、张伐、石挥、冯喆等。若是有同学从照相馆或地摊上偶尔购得一帧明星的黑白小照,抑或是十余位明星上下左右拥挤地排列在同一张五寸照片上,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阮玲玉、徐琴芳、胡蝶、胡珊、白光、王人美、黎莉莉、李丽华等,则全班会为之轰动。与今日身价千万却仅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影视明星们相比较,他们可谓是“常青树”了。
那时候,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大多是富有革命教育意义的,如《上甘岭》《铁道游击队》《党的女儿》《李双双》《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51号兵站》等。男同学大多爱看反特电影,诸如风靡那个年代的《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古刹钟声》《天罗地网》《徐秋影案件》《国庆十点钟》等,但这一类电影偏偏学校组织得不多,实在要看,唯有自己掏腰包了。
大概是受了这些反特影片的影响,我们男孩子当时满脑子都是“抓特务”。结果,有一天晚上,真的遇上了“特务”。记得那是夏天,我们几个邻居兼同学正在纳凉,看到一个腋下夹着皮包的青年男子围着前面一幢工房转来兜去,立即引发了我们这些男孩的高度警惕,纷纷围上去询问。
可想而知,我们的语调肯定算不上十分友好。那青年男子颇为警觉地看了看我们,忽然问:“你们都是少先队员吗?”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以后,他笑了,说:“你们能保守秘密吗?”见我们大惑不解,他犹豫了一会儿才说:“我在执行任务,我是公安局的便衣警察。”
目录:
第一章 跨界行动·工人新村 / 1
第二章 野蛮小鬼·瞎白相 / 17
第三章 书呆子·大种十边 / 33
第四章 困难时期·鹅鹅鹅 / 51
第五章 抓特务·资本主义尾巴 / 67
第六章 竹笛横吹·学工学农 / 87
第七章 风乍起·吹皱春水 / 103
第八章 逍遥派·练武习文 / 115
第九章 矿石收音机·“工人一哥”/ 135
第十章 毕业分配·进工矿 / 149
第十一章 扎根工厂·火红年代 / 169
第十二章 往事如烟·记忆不灭 / 197
第十三章 十年一觉·大学梦 / 219
第十四章 告别新村·重返弄堂 / 255
后 记 / 276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