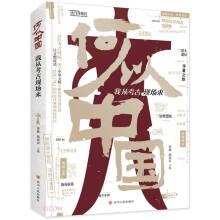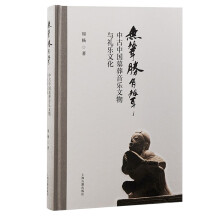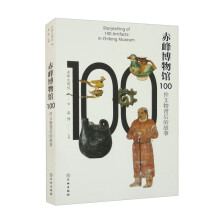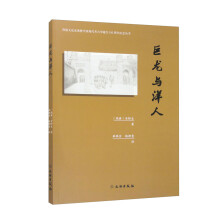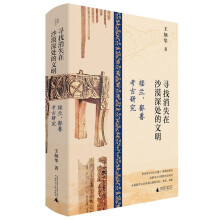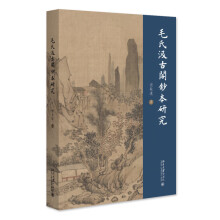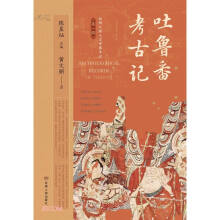尚未破解的秘密:巴蜀图语
上古时期的巴蜀先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巴蜀古文明,在农业生产、青铜制造、城市建筑、商业贸易等众多领域都取得过重大的进步和辉煌的成就,辉煌而神秘的三星堆遗址就是极好的证明。世人在欣赏赞叹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疑问:巴蜀先民既然创造了如此灿烂辉煌的文明,是否也产生、创制了自己的古文字呢?如果创造了文字,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
早在汉、晋之时,人们就对于巴蜀是否有其文字发生过重大的争论。但直到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巴蜀青铜器的不断发现和巴蜀考古的逐渐深入,出土的实物资料日益丰富,才使问题的讨论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但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这些所发现的实物资料,它们究竟是符号,是图案,还是文字?如果是文字,又如何破译?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是采用一个笼统的称谓——“巴蜀图语”。
所谓“巴蜀图语”,有的学者认为,其单符的象形直接提供了“看图识字”或“望文生义”的直觉感;因此,所谓“图语”即是“图像的语言”。
已经发现的“巴蜀图语”资料,主要是在湖南、四川等地出土的青铜戈上的铭文。这些青铜戈都具有巴蜀戈的独有特征,它们毫无疑问是属于巴蜀先民的物品。而青铜戈上的五十余个铭文,其字形结构相同,可以断定是属于同一个古文字系统的。换句话说,青铜戈上与巴蜀纹饰和符号一同出现的铭文,它们就是巴蜀古文字。
通过对巴蜀青铜戈上铭文的字形和基本结构研究分析,发现巴蜀古文字与汉语古文字有着明显区别。从其方块字形来看,这种文字“似汉字而又非汉字”,其“基本偏旁结构和汉字有别”。上述巴蜀古文字都不能运用汉语古文字的方法予以解读,这也反过来说明它是不同于汉字的另外一个古文字系统。
据分析,这些有铭巴蜀青铜戈的年代,其上限早到春秋晚期,下限则在。战国末叶秦统一巴蜀以后。当然,这只是一个参考年代,因为青铜戈的制作年代并非就是巴蜀文字的发明年代。从字形的发展演变规律考察,巴蜀方块字发展到如此程度,它的起源必定还会早得多。有的学者认为,至少在商代晚期,巴蜀方块字不但已经产生,而且趋于成熟。
除上述有铭巴蜀青铜戈外,在四川的其他地方,比如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也发现了“巴蜀图语”资料。如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些陶器上,发现有刻划符号。有的是X形符号,有的是一形符号;有的单独出现,有的三枚成组,有的两组对称。显然,这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并不是偶然的人工刻划痕迹。同一种符号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这一现象说明这些符号及其含义已经固定化了,已经约定俗成了。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代表着较早期的古文字。
在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了一件陶纺轮,其腰部刻有两字。有的学者认为,这两个字与三星堆2号坑牙璋上的文字一样,也是抽象化、线条化了的方块表意文字。
研究者认为,巴蜀文字可以按其特点分为两系,~为方块表意文字,一为符号象形文字。巴蜀方块字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而其滥觞还应予以提前。巴蜀符号的起源晚于方块字,目前只能将滥觞期追溯到商代晚期。两系巴蜀文字均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大量使用,成为巴蜀境内并行不悖的两大系列文字。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字仍继续使用、流传。秦始皇推行文字统一制度,但直到汉初,巴蜀文字仍屡有所见,直到汉中叶后,作为一个文字体系,才日渐消失。
2007年,凉山州语委古籍科科长、古彝文专家阿余铁日提出了另外一种新颖的说法。他认为,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巴蜀图语”是古彝文。据他所说,他于2006年10月到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考察,当他看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巴蜀图语”时,顿时震惊了:在他看来,这些“巴蜀图语”是那么的亲切,冥冥之中他觉得那就是古彝文。回到凉山后,他又搜寻了更多的资料进行对照。于是,“巴蜀图语”是古彝文的想法便产生了。
“巴蜀图语”究竟是不是文字,究竟是不是古彝文?如果是文字,又该如何破译?凡此种种,依然需要进一步考证与研究。我们相信,“巴蜀图语”在被完全成功解读之后,关于巴蜀古文明的许多谜团将迎刃而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