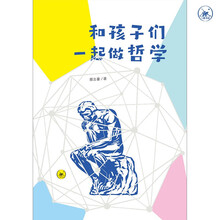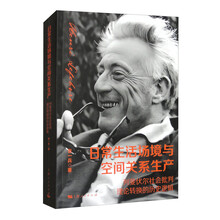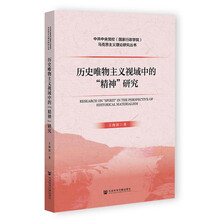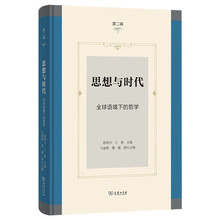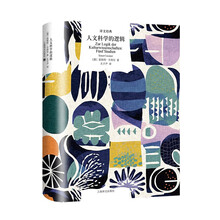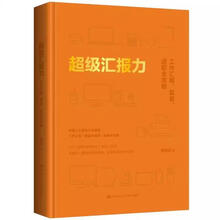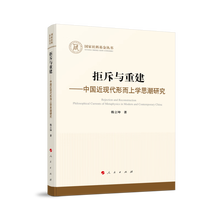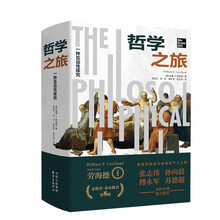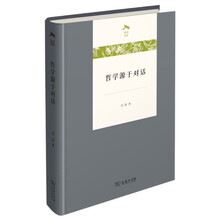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朱维铮学术讲演录》:
况且所谓经原属通称。《国语·吴语》称“挟经秉袍”,是兵书称经。《管子》有“经言”“区言”,则教令称经。《论衡·谢短》谓“五经题篇,皆以事义别之,至礼与律独经也”,则法律称经。《汉书·律历志》序庖牺以来帝王代禅为《世经》,则帝系称经。《隋书·经籍志》记有挚虞《畿服经》,是辨疆域的“图经”,则地志称经。至于诸子称经更多。《墨子》有《经上》《经下》;《韩非子》著内外《储说》,标署纲目为“经”;《老子》在汉代有邻氏次为经传;《荀子》中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语,也不见于“五经”。汉人称自己著作为经,如贾谊著《容经》,扬雄著仿《易》的《太玄经》,与扬雄同时的阳城子长作《乐经》(见《论衡·超奇》)。章太炎曾据这些例子驳章学诚所谓“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因非扬雄、王通(著《元经》)的说法,是合于历史的。
清代阮元说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明古代文以耦俪为主,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清末刘师培因袭此说,以为骈俪的韵文称经。章太炎驳之,谓《春秋》经传均称文;司马迁谓“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则律令礼仪均称文。屈原赋有韵,而称《楚辞》。这都表明以文体称经不当。
不过章太炎对经下的定义也未必当:“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传者,专之假借。《论语》‘传不习乎’,《鲁》作‘专不习乎’。《说文》训‘专’为‘六寸簿’。簿即手版,古谓之忽(今作笏)。书思对命,以备忽忘,故引伸为书籍记事之称。书籍名簿,亦名为专。专之得名,以其体短有异于经。”原注说古官书长二尺四寸,经与律均官书,传简长六寸谓“短书”。“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传,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也。”(《国故论衡》中《文学总略》)但此说也有问题。古代写书之质料,既有简牍,也有缯帛,更早还有龟甲金版,故范文澜尝说经即金的借字,指铸在金版上的书籍(见《群经概论》,后范弃此说)。而事实上经愈来愈成为所谓孔子著作的专名,怎么解释呢?
周予同先生另提定义:“经是中国儒教书籍的尊称,因历代儒教徒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以经的定义逐渐演化,经的领域也逐渐扩张,由相传为孔子所删订的《六经》扩张到以孔子为中心的其他书籍,如《孟子》、《尔雅》等。”(《群经概论》一九三三年商务版,第四页)
我以为周先生的定义,长处在于指出了经的范围以孔子为中心,经的领域限于儒家书籍,且有变化过程,但也有缺陷。定义无非是客观事物的抽象概念。抽象概念的形成包含着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联系的意识。因而,给事物下定义,要注意它的普遍性,更要注意它能反映现象后面的本质,而本质即规律性,是由支配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周先生定义的缺陷,正在于还没有脱离直观的现象的范畴,因而不能反映封建时代经典的本质方面。
封建时代经典的本质方面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自西汉立五经博士并置弟子员,从中选拔官吏,并以“通经致用”作为考核官吏优劣的标准,这以后所谓经就逐渐变成封建国家规定的官方教科书,而且是具有神学性质的教科书。宗教教义的特点是只许信仰不许怀疑,因而被列为经后即一字一句也不许更改,乃至将伪书奉作真经,如《伪古文尚书》即被当作孔子手订的东西而被封建统治者强迫诵习了一千多年,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自是实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