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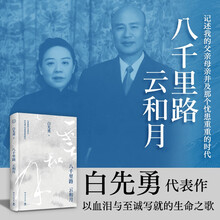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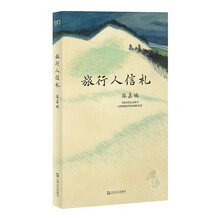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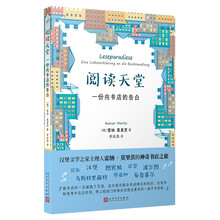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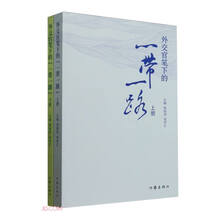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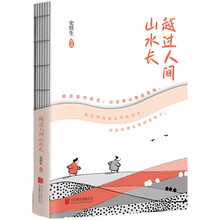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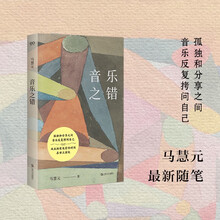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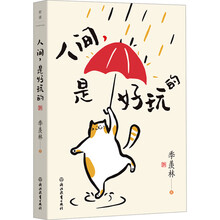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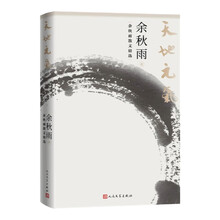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张爱玲
张爱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贵族出身。对于这一点,我始终不以为然。文学的事,永远不可能如此简单。贵族出身的人实在太多,张爱玲的家庭了不起,比她更显赫的家族并不在少数。并不是破落的大家子弟,就应该注定成为曹雪芹。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其次还是因为她的作品。作品是人创造的,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作品可以反过来改变一个人的。作家成就了文学,文学也会毫不含糊地创造一个人。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部大作品。多少年以后,这部作品也许比什么都重要。早在二十五岁以前,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就用得差不多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传奇》和《流言》,都是在这之前完成的。很多文学青年在这个年纪,还没有来得及开窍。张爱玲是文学早熟又一个奇迹般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托马斯·曼,他在这个年龄完成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张爱玲喜欢用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来形容她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二十五岁以后,她断断续续还在写,我几乎见到过以后的所有作品。我不至于说她的《红楼梦魇》不妥,那些言情的电影剧本意义不大,从方言改成语体文的《海上花列传》是浪费时间,事实证明这也很了不起,然而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一样,就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
我猜想张爱玲把自己也变成了作品中的人物。这正是她的高明之处。有意或者无意,她突然明白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自己。她结过两次婚,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但是显然不理想。一个是有才华却太轻薄的汉奸,一个是西方的左派作家,不能否定她和他们在沟通上的那种障碍。张爱玲选择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小说作法。小说作法有时候也会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我猜想许多事,张爱玲都是存心的。她存心要我们为她感到无穷无尽的遗憾,要我们痛苦地去回味她走过的人生。她存心要我们喋喋不休地去争论她为什么放弃了小说,为什么不思如泉涌没完没了地写下去,要我们为许多站得住脚和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唾沫和笔墨。她存心要我们哭笑不得,要我们疑惑不解,要我们很快地忘记她,而实际上却永远也不可能把她遗忘。
二
以上是应香港一家报社的约稿,写了一篇谈张爱玲的文章。言犹未尽,总觉得还可以再说些什么。张爱玲这样的才女,照例是很容易作为闲话的话题。一个女作家本来就引人注目,更何况张爱玲作品之外,还有那么多故事。
就说张爱玲的成名。她自称九岁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打算把自己在杭州写的日记,寄给编辑先生。张爱玲用稚嫩的语气,写了一封没有标点的信,扔在信筒里,从此没有下文。十九岁的时候,她参加了《西风》的征文活动,在六百八十五名应征者中,有十三人得奖,这次编辑总算没有太走眼,张爱玲名列倒数第一,正好第十三名。按照征文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只有十名,多出来的三名是荣誉奖。张爱玲参赛的作品叫《天才梦》,这可能是张爱玲文字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不过张爱玲对自己的名次耿耿于怀,她成名后,谈起这段往事,坚持说名列第一的那篇文章实在平平。
张爱玲给人的印象,在一夜之间突然就红了。女作家的走红向来比男作家凶猛。在张爱玲成名的十几年前,丁玲女士也是如此。记得读研究生时,一位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极有成就的老师说过,丁玲一出现,她几乎就取代了冰心女士的位置,冰心火爆得更早,这种取代之说有些夸张,也不准确,但是有纪实的一面。张爱玲的出现,也有取代丁玲之势。冰心的文章以爱心和提出问题取胜,丁玲却是以她的反叛和浪漫精神获得读者,张爱玲和她们都不一样。张爱玲的小说要丰富得多,而且她显然不喜欢她的两位前辈。
张爱玲的小说深入到了平常人的心灵,这是她的小说能拥有无数“张迷”的法宝。真正的好作品是阻挡不住的,张爱玲的小说最初发表在文坛不屑于注视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许多有志向的文学青年绝对不会去理睬这样的刊物。张爱玲偏偏什么都不在乎。她似乎信奉小说只要能发表就行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小说之外的事,不愿意想得太多。她的小说在什么刊物上都可以出现,譬如发表她小说最多的是《杂志》,这个刊物显然有日本人的背景。在沦陷时期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张爱玲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她火山爆发一般地拼命写,写了就拿出去发表。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张爱玲就这样成了名,她的文章得到了当时上海滩各种背景的刊物的欢迎。转眼之间,她成了真正的名家。
晚年的张爱玲和四十年代大红大紫的张爱玲,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晚年的张爱玲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杜门谢客,摈绝交游,以至于最后死在美国公寓的地毯上,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那样地爱出风头,她为了突出自己,甚至不惜身着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动机非常简单,写东西就是为了要出名,越早越好,越大越好。遗憾的是张爱玲有出风头的心,没有出风头的命。她不是那种能够当交际花的女人,倒不是长得不漂亮,实在是不善于人际交往。她的骨子里讨厌交际,在大红大紫的年代里,她不能免俗地参加各种应酬,出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尽情地品尝自己成功的喜悦,然而这些无聊的敷衍已经为她日后隐士般的生活留下伏笔。
张爱玲的奇迹在于当年引起了各路人马的叫好。她毫无选择地在各种刊物上乱发表文章,属于不同阵营的编辑却非常明确地想把她拉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张爱玲的小说终于出现在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上,这虽然是一本商业性杂志,但是 在柯灵的努力下,杂志明显地属于新文学阵营。当年柯灵先生为如何能约到张爱玲的稿子踌躇再三,出乎意外,张爱玲竟然冒冒失失自动送上门。多少年后,柯灵谈起这段往事仍然喜形于色。
很多有识之士出于爱护张爱玲的缘故,反对她这样无原则地是地方就乱发文章。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具体的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先付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张爱玲根本就不理这一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的名言仍然是那句: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相信她的小说可以远离政治。可是潜意识里知道这绝不可能,要不然她不会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也许是张爱玲真正的高明之处。如果她真听了郑振铎的话,把自己的小说藏之名山,等日本人完蛋再发表,结局也许更糟糕。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也就只有抗战胜利前的两年时间,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张爱玲后来死灰复燃,文坛上再次走红,先是在台湾,然后在大陆。她的书成了畅销书,让出版社趁机赚钱。“张迷”成为一个固定词组,重要的原因,是她在那个特定时期写的并且毅然发表的小说《传奇》和散文《流言》。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就是这么滑稽。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陈旧人物”既代表人的陈旧,也试图把“陈”当作动词,展览一下几个老掉牙的前辈。
——叶兆言
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
——苏童
由于叶兆言的家学渊源,他写到了祖父和父亲与那些名家中一些人的交往,也写到了他自己的有趣经历,都是难得的史料。尽管此书是随感札记的形式,却比学院派的那些高头讲章更能引领读者走近那些“陈旧人物”,理解那些“陈旧人物”。
——陈子善
叶兆言无疑是当今作家中*适合写这些文字,既有家学渊源知道很多掌故,又有小说家的细腻文笔——往往几笔就把一个老派人物勾勒的活灵活现。
——豆瓣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