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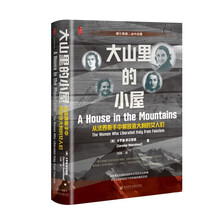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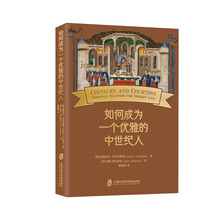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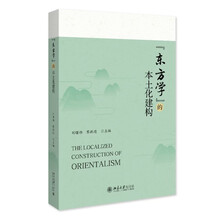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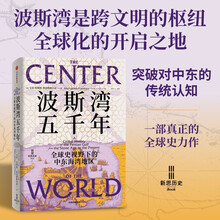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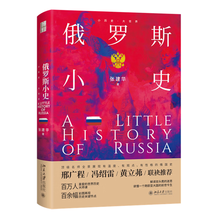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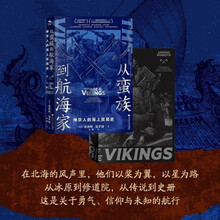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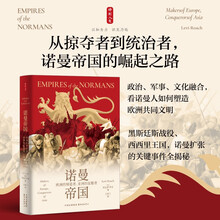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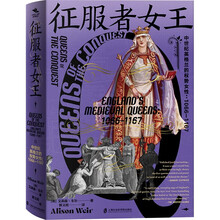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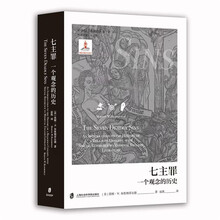
度量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人们对此依赖有加,却又习以为常。
人类的身体是一个计量用具,自远古以来,不同国度的人们都曾经利用粮食粒和种子粒随机制作测量长度和重量的量具。本书深入探究了全球度量系统的发展历史,从中国古代的尺子和笛子讲到了西非的黄金砝码,从法国人发明的长度标准、英国人发明的英制单位讲到了公制计量的演进。作者描述了国王、革命家以及学者如何制定通用的度量标准,现代科学家对于精度的孜孜以求,这些对于支撑全球的科学、技术和商贸发展都意义重大。
温馨提示:请使用青岛市图书馆的读者帐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第八章您肯定是在开玩笑,杜尚先生 这是跟“米制”开的玩笑。——马塞尔·杜尚 马塞尔·杜尚漫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第五层的画廊里,人们可以欣赏到一些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的著名的艺术品。例如,某个房间里悬挂着文森特·威廉·梵·高的《星月夜》,另一个房间里悬挂着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第三个房间里悬挂着亨利·马蒂斯的《舞蹈》。还有一个房间,满屋子挂的都是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包括《百老汇爵士乐》,其他作品似乎都出自巴勃罗·毕加索的手笔,包括一幅《亚维农少女》。沿楼梯上行至某楼层顶端的平台,角落里有个小画廊,屋里的作品制作得相当与众不同,屋子中央摆放着《自行车轮》,那不过是个自行车轮,架在倒置的前叉上,前叉立在一个就餐用的凳子上。这件作品出自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之手,他声名大噪的一大原因是人们对他的许多作品一直存在争议。例如,《泉》——那是个陶瓷小便池,杜尚在小便池边缘签了个假名;再如L.H.O.O.Q.,是一个《蒙娜丽莎》的复制品,杜尚的画只不过比原画多了上髭和山羊胡。杜尚将《自行车轮》称为“成品”,也即他选择的某个日常用品,为其添个名目,然后将其称为艺术品。房间里有个靠墙而立的玻璃柜,柜子里是杜尚另一件耐人寻味的作品,名为《三个标准器的终止》。这件作品包括一个开着盖子的槌球盒,盒子里没有球棒,而是两条又薄又长、看起来像玻璃的“胶片”袋,每个胶片袋里有一根固定在帆布条上的弯弯曲曲的长线,盒子里还有两根破木条,盒子上方的半空中吊着个内装长线的胶片袋,以及一根破木条。设在柜子旁边的文字说明牌标注着:本作品制作于1913—1914年,“这是跟‘米制开的玩笑’,这是杜尚对这件作品油腔滑调的注解,不过这一注解有个前提,大致隐含着如后定理:‘假设1根1米长的直线从1米高平行掉落到一个平面上,掉落过程任其自由扭曲,它会创造出一个新的长度单位形象。’”说明里还写着:“杜尚让三根1米长的线从1米高掉落到三个长长的帆布条上,然后将这三根线固定在帆布上,以便保留它们随机掉落在平面后的弯曲,帆布条是沿着线的走势剪裁的,制作出的模板即是线的各种弯曲——这样就随机创造出了新的度量衡单位,既保留了米的长度,又颠覆了它的合理基础。”这件绰号《终止》的作品的确很奇怪,它的文字说明更让人振聋发聩。合规的“米”是国际单位制的基本计量单位,是国际单位制的创造者们,也即法国的革命者们视之为科学性和政治性解放的“米”。这件艺术品真能阻止米制吗?或者,它不过是杜尚派人士的又一次调侃。从说明牌来看,博物馆馆长们并未意识到其中的讽刺:艺术家讽刺的是人们对精准和普世的痴迷。而且,是艺术家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因为他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冷眼旁观的参观者很可能会以为,艺术家的这件作品跟科学根本扯不上关系。杜尚对科学、公制计量体系、度量衡有多少了解,是什么促使他制作了这个物件?若想知道答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初期那些年,其时科学界正处于爆发时期,杜尚正在长大成人。 科学引发的焦虑20世纪初,令人惊异的科学发现(X射线、放射现象、电子等)和强大的新技术(电气化、无线电报等)正颠覆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固有观念。虽然杜尚从小接受绘画训练——为了成为艺术家,他17岁便跟着两个哥哥来到巴黎,但他和其他非科学家们乐于接受一切与科学有关的事物,因为当时高质量的科普活动很多。科学家们,例如玛丽亚·居里(Marie Curie)和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等人经常在畅销杂志上简明扼要地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他人诸如让·皮兰(Jean Perrin)和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写了许多畅销书。大众文化里充满了科学气息。亨利·庞加莱在1902年出版了《科学与假设》(Science and Hypothesis),截至1912年,这本书已经重印二十次。庞加莱雄辩地说明,近期的科技进步正在动摇牛顿的力学基础,人们甚至对科学的客观观念产生了质疑。人们将庞加莱倡导的哲学态度称为“保守主义”,这一态度认为,几何图形和所有科学定律其实都是为了方便人类——无论是心理投射还是理论框架——而不是为了如实解释大自然,这种想法必将深刻地影响诸如杜尚这样的艺术家。《科学与假设》之类的书籍激发了一种文化焦虑:科学承诺给人类的似乎是稳定性——全世界处于一种秩序井然的、力学无所不在的情景中,拥有可靠的和强大的技术,还有不断增加的物质享受;基于各种机构和协议的国际合作机制日益扩大,重建整个人类社会指日可待。不过,欧洲却在慢慢地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苗头显示,前述的美好憧憬可能无法实现。其实,机械情景并非不存在混沌现象,技术也并非无害,物质享受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当。法国诗人兼文学评论家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用似是而非的文笔表达了人们的上述矛盾心态。他是这样表示的:人类向往秩序,却在创造无序;人类追求美德,却在制造恐怖;人类探索合理,却在孕育无理。瓦雷里没有专门举例说明他讲的是什么,不过他极有可能讲的是“量子”概念——这一概念出现时,人们正在千方百计地整理热力学的细枝末节。诗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疯狂地追求精度”正在将人类引向反面,进入这样的状态:“宇宙正处于分裂进程中,已经毫无希望归于一体,超显微状态下的世界与人们平日所见大相径庭。对宿命论来说,这导致了因果关系的危机。”瓦雷里更加肆无忌惮地说道:“科学之力正在征服整个世界,导致所有领域都无法预测了。”在他眼里,科学的冲击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能感受到,他曾经预言“人类的艺术概念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认识到,他们与科学有着不解之缘,艺术领域发人深省的发现总会成为头版新闻,而且会对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观念形成挑战。当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第四维度,当时人们想到的是时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维度(1919年,广义相对论证实许多预言后才有了时间维度)。当年,许多小说家、音乐家、画家意识到,这一想法令人兴奋,大开眼界。对一种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人们可以看透其内部;对另一种人来说,它意味着多重透视效果的确存在;对第三种人来说,的确存在唯有艺术家的直觉才能感悟和揭示的现实秩序。第四维度的大部分影响源自X射线的发现,真有处于人类视觉之外的看不见的结构,X射线让这些结构不再是哲学家笔下形而上的东西,不再是神秘术士的幻想,反而成了科学事实。
马塞尔·杜尚漫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第五层的画廊里,人们可以欣赏到一些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的著名的艺术品。例如,某个房间里悬挂着文森特·威廉·梵·高的《星月夜》,另一个房间里悬挂着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第三个房间里悬挂着亨利·马蒂斯的《舞蹈》。还有一个房间,满屋子挂的都是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包括《百老汇爵士乐》,其他作品似乎都出自巴勃罗·毕加索的手笔,包括一幅《亚维农少女》。沿楼梯上行至某楼层顶端的平台,角落里有个小画廊,屋里的作品制作得相当与众不同,屋子中央摆放着《自行车轮》,那不过是个自行车轮,架在倒置的前叉上,前叉立在一个就餐用的凳子上。这件作品出自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之手,他声名大噪的一大原因是人们对他的许多作品一直存在争议。例如,《泉》——那是个陶瓷小便池,杜尚在小便池边缘签了个假名;再如L.H.O.O.Q.,是一个《蒙娜丽莎》的复制品,杜尚的画只不过比原画多了上髭和山羊胡。杜尚将《自行车轮》称为“成品”,也即他选择的某个日常用品,为其添个名目,然后将其称为艺术品。房间里有个靠墙而立的玻璃柜,柜子里是杜尚另一件耐人寻味的作品,名为《三个标准器的终止》。这件作品包括一个开着盖子的槌球盒,盒子里没有球棒,而是两条又薄又长、看起来像玻璃的“胶片”袋,每个胶片袋里有一根固定在帆布条上的弯弯曲曲的长线,盒子里还有两根破木条,盒子上方的半空中吊着个内装长线的胶片袋,以及一根破木条。设在柜子旁边的文字说明牌标注着:本作品制作于1913—1914年,“这是跟‘米制开的玩笑’,这是杜尚对这件作品油腔滑调的注解,不过这一注解有个前提,大致隐含着如后定理:‘假设1根1米长的直线从1米高平行掉落到一个平面上,掉落过程任其自由扭曲,它会创造出一个新的长度单位形象。’”说明里还写着:“杜尚让三根1米长的线从1米高掉落到三个长长的帆布条上,然后将这三根线固定在帆布上,以便保留它们随机掉落在平面后的弯曲,帆布条是沿着线的走势剪裁的,制作出的模板即是线的各种弯曲——这样就随机创造出了新的度量衡单位,既保留了米的长度,又颠覆了它的合理基础。”这件绰号《终止》的作品的确很奇怪,它的文字说明更让人振聋发聩。合规的“米”是国际单位制的基本计量单位,是国际单位制的创造者们,也即法国的革命者们视之为科学性和政治性解放的“米”。这件艺术品真能阻止米制吗?或者,它不过是杜尚派人士的又一次调侃。从说明牌来看,博物馆馆长们并未意识到其中的讽刺:艺术家讽刺的是人们对精准和普世的痴迷。而且,是艺术家对此有足够的敏感,因为他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冷眼旁观的参观者很可能会以为,艺术家的这件作品跟科学根本扯不上关系。杜尚对科学、公制计量体系、度量衡有多少了解,是什么促使他制作了这个物件?若想知道答案,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初期那些年,其时科学界正处于爆发时期,杜尚正在长大成人。 科学引发的焦虑20世纪初,令人惊异的科学发现(X射线、放射现象、电子等)和强大的新技术(电气化、无线电报等)正颠覆性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固有观念。虽然杜尚从小接受绘画训练——为了成为艺术家,他17岁便跟着两个哥哥来到巴黎,但他和其他非科学家们乐于接受一切与科学有关的事物,因为当时高质量的科普活动很多。科学家们,例如玛丽亚·居里(Marie Curie)和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等人经常在畅销杂志上简明扼要地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其他人诸如让·皮兰(Jean Perrin)和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写了许多畅销书。大众文化里充满了科学气息。亨利·庞加莱在1902年出版了《科学与假设》(Science and Hypothesis),截至1912年,这本书已经重印二十次。庞加莱雄辩地说明,近期的科技进步正在动摇牛顿的力学基础,人们甚至对科学的客观观念产生了质疑。人们将庞加莱倡导的哲学态度称为“保守主义”,这一态度认为,几何图形和所有科学定律其实都是为了方便人类——无论是心理投射还是理论框架——而不是为了如实解释大自然,这种想法必将深刻地影响诸如杜尚这样的艺术家。《科学与假设》之类的书籍激发了一种文化焦虑:科学承诺给人类的似乎是稳定性——全世界处于一种秩序井然的、力学无所不在的情景中,拥有可靠的和强大的技术,还有不断增加的物质享受;基于各种机构和协议的国际合作机制日益扩大,重建整个人类社会指日可待。不过,欧洲却在慢慢地滑向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苗头显示,前述的美好憧憬可能无法实现。其实,机械情景并非不存在混沌现象,技术也并非无害,物质享受也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当。法国诗人兼文学评论家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1871—1945)用似是而非的文笔表达了人们的上述矛盾心态。他是这样表示的:人类向往秩序,却在创造无序;人类追求美德,却在制造恐怖;人类探索合理,却在孕育无理。瓦雷里没有专门举例说明他讲的是什么,不过他极有可能讲的是“量子”概念——这一概念出现时,人们正在千方百计地整理热力学的细枝末节。诗人的原话是这么说的:“疯狂地追求精度”正在将人类引向反面,进入这样的状态:“宇宙正处于分裂进程中,已经毫无希望归于一体,超显微状态下的世界与人们平日所见大相径庭。对宿命论来说,这导致了因果关系的危机。”瓦雷里更加肆无忌惮地说道:“科学之力正在征服整个世界,导致所有领域都无法预测了。”在他眼里,科学的冲击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能感受到,他曾经预言“人类的艺术概念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认识到,他们与科学有着不解之缘,艺术领域发人深省的发现总会成为头版新闻,而且会对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的观念形成挑战。当年的一个热门话题是第四维度,当时人们想到的是时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维度(1919年,广义相对论证实许多预言后才有了时间维度)。当年,许多小说家、音乐家、画家意识到,这一想法令人兴奋,大开眼界。对一种人来说,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人们可以看透其内部;对另一种人来说,它意味着多重透视效果的确存在;对第三种人来说,的确存在唯有艺术家的直觉才能感悟和揭示的现实秩序。第四维度的大部分影响源自X射线的发现,真有处于人类视觉之外的看不见的结构,X射线让这些结构不再是哲学家笔下形而上的东西,不再是神秘术士的幻想,反而成了科学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