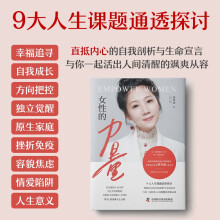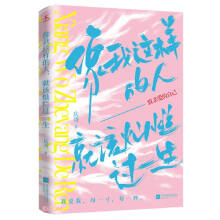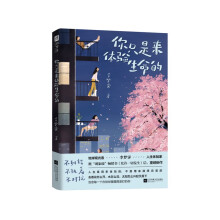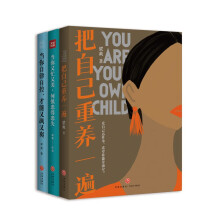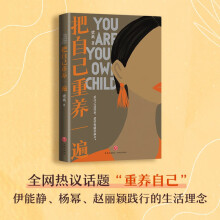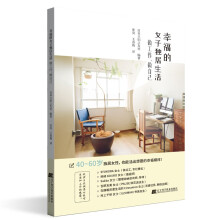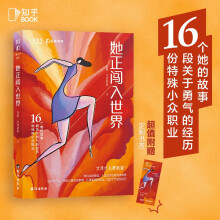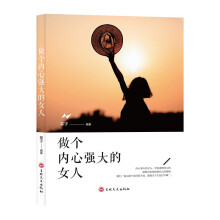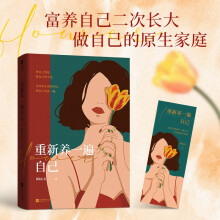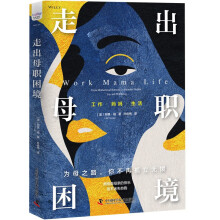《淡定的女人最优雅》:
永远保持在路上的状态
看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这本小说的女性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阅读此书仿佛是一场旅行的开始,听作者诉说着青春的激情,或飞扬,或沉沦,在喜悦的心情中欣赏主人公们漫游的传奇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迪安带领萨尔等人开始了一场看似盲目的旅行。一路上,他们搭车赶路,结识陌生人,放纵性情,随心所欲,在聚众旅行的狂欢中,几乎没有道德底线,即使落魄如乞丐,但只要“在路上”就是惬意的。
书中的人物不停地穿梭于公路与城市之间,每一段行程都有那么多人在路上,孤独的、忧郁的、快乐的、麻木的……纽约、丹佛、旧金山……城市只是符号,是路上歇息片刻的驿站,当他们抵达一个地点,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于是只有继续前进。
作者曾经借书中迪安之口对萨尔发问:“……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这也正是对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提问,它以无与伦比的诱惑吸引着无数人上路。
《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
如今,“在路上”已经成为一种追逐精神自由飞扬的符号。背起行囊激动地上路,探求不可预知的旅途,人们似乎就可以“掌握开启通向神秘的种种可能和多姿多彩的历练本身之门”,“在路上”更像是一种不安现状,奔赴梦想,寻找彼岸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女人也开始去大自然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不再把自己的人生局限于某个办公楼的写字间,不再一直扮演着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更喜欢“在路上”的感觉,行进在路上,甚至不问还有多远,还要走多久,她们只是留恋路上的风景,无论美丽的抑或残酷的,只是追逐一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
尹珊珊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美女作家,在北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在中央戏剧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如今是一位时尚、读书专栏作家,写博客爱好者;也是一位旅行狂人、阅读狂人、赚钱狂人。她说每个女人都应该关注时尚,而不盲目追逐时尚。只要有机会就该给自己时间去更多的地方。同时,“幕后是我的工作性质,阅读是必需的习惯”。
尹珊珊认为女人的品质生活与真正的智慧有关,这来源于她坚持每天阅读的习惯。每一年,她都会利用“卖文”积攒下来的稿费到世界各地旅游,把满满的钱包变成一段段关好的回忆。
2010年,尹珊珊去了北极,在24小时的极昼中,她不小心把拍摄的照片都弄坏了。虽然很遗憾,她说:“记忆在大脑中是不会磨损的,这就够了。”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以购买收藏品来巩固记忆,寄回国的过程中这些收藏品往往会遗失大半,此时她总乐呵呵地劝慰自己:“你曾经拥有过它们了,不是吗?”
尹珊珊认为只要你有梦想就一定要去实现,哪怕在别人看来那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也要去做,否则就会留下遗憾。她一直很欣赏电影导演伯格曼,特别希望见到他本人,于是留下给瑞典皇家戏剧学院写了封信,对方竞然答应了她的这个请求。当时伯格曼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不接受记者的邀约,但是因为她的会见请求属于“学术性质”,所以伯格曼同意见面,她也由此见到了偶像。后来没有多久,伯格曼就去世了。
尹珊珊说她最大的梦想是去智利最南端的海角——合恩角,在电影《春光乍泄》里提到的“世界最遥远的灯塔”就在那里。这个地方非常不容易到达,堪称航海界的“珠穆朗玛峰”。她甚至想过在脖子上挂一个牌子,写上:“只要你可以带我去合恩角,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如果不是心中最渴望实现的想法,绝对说不出如此疯癫的言语。
尹珊珊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在路上”的女博士,一个坚持与文字、旅行舞蹈的人。行走是她一贯的姿势,路途中她循着内心的意愿,永远一往无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