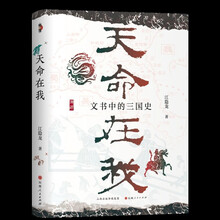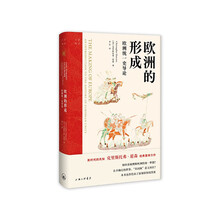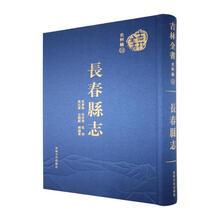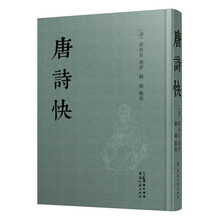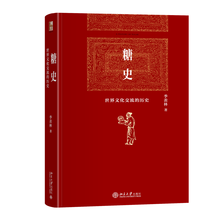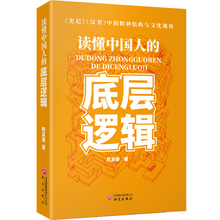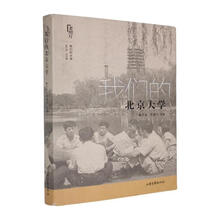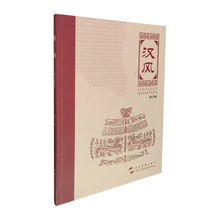清明忆父
父亲屈怀远是在母亲王玉琴走后第四个年头撒手人寰的。倘若老人家健在,今年应是103岁的人间仙翁了。
令我至今无法释怀的是1979年4月5日,父亲刚跨进63岁的门槛,便走到他艰辛凄苦的人生终点。
今年的清明节,是父亲的忌辰。清明与忌辰重合,这是因缘际会,抑或是天人巧合,我难以判定。但我相信吉人天阀,一善有善报,父亲能够分享青冢弹泪的天下追思,也算是一种哀荣!可我宁愿父亲活着,也不要这样的哀荣。
我是在父亲告别尘世前十多天离开他的。那时候父亲已经猜到他得了不治之症,而父子之间的诀别,无疑使死亡早几天掐住了父亲的命门。父亲靠在我弟弟身上,倚门送我时寸步难移。他时而点头,时而摇头,浑浊的眼眶装满了不舍,绝望的神情笼罩着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那一刻,我们父子相对流泪,没有说一句话。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呢?只有生离死别的悲痛,只有忠孝不能两全的心声!那一刻早已长进我的脑子,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是在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凯旋声中走向生命终点的。
1979年2月17日,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全线打响,3月16日我军全部撤回国内。3月20日,我受命前往成都军区政治部政研科,学习部队战前和作战期间的政治工作经验。
那时候,南线作战虽然胜利结束,但乌鲁木齐军区所属部队仍然处于临战状态。军区首长判断,虎视眈眈的对手很可能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我边境地区或浅近纵深,替一败涂地的越南报复我军,因为苏越两国刚刚缔结完同盟条约。此前,嚣张的黎笋集团敢于置我国再三警告而不顾,频繁侵犯我边境,故意杀害我边民,就是仗着这一纸条约壮胆的。
为了防止苏军后发制人,乌鲁木齐军区所属部队枕戈待旦,剑拔弩张,在“南疆部队放鞭炮,新疆战备不松套”的动员声中,加紧防敌突袭的准备工作。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专程到成都军区取经的。
父亲虽然只有初小文化程度,但当过石印IA,识字不少,对《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弟子规》等启蒙读本比较熟悉,也了解其中一些典故。同时受关中乡土观念的影响,对南方“蛮子”颇不待见。1961年,听说我参军要去四川,父亲当时坚决不同意。理由是“老不出关”。后来又听人说“娃到四川不想家,又有媳妇又有妈”,更不同意我当兵入川,担心我到四川娶妻生子,乐不思秦。第二年得知我去新疆当兵,虽觉得远隔天涯,但没有阻拦,只是要我尽完三年义务再回来读书,多长点出息,多学点能耐。
得知我当干部后,父亲没再劝我重回学校读书,但对新疆局势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常人。新疆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求我务必给家里写信。1970年11月,新疆部队战备,家属紧急疏散。父母得知消息后,连发电报催我把孩子送回老家。鉴于战备形势日趋严峻,正在坐月子的妻子孙兰带着刚满两岁的女儿和满月的儿子,乘了56小时的火车回到白鹿原,把孩子托给父母抚养。将近两年时间,我们既没顾上回去看望父母,也没顾上把孩子接回新疆。P3-5
展开